时晓、杨明星 |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核心话语分析
本文原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3期。感谢作者时晓老师、杨明星老师和《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支持。


提要: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典入手,全面考察其翻译思想的核心话语。这些话语可概括为:1)五大理念:翻译的科学属性、政治属性、传播属性、认知属性和创造属性;2)四大翻译伦理:坚持政治忠诚、恪守职业道德、强化职业素养、倡导语言多元平等;3)六大翻译原则:忠实流畅、风格再现、活力等效、精神传播、受众理解、用语统一;4) 八大翻译策略:造词译法、逐字译法、加注译法、删减译法、改写译法、形象译法、回译法、活译法。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主要源自其翻译实践、语言哲学和政治思想。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翻译理念、翻译伦理、翻译原则、翻译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外文撰写和翻译工作,二人在书信往来和专文中对翻译标准、译者行为、翻译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构建了自成一体的翻译思想体系。
前民主德国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结集出版,命名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风格与翻译》(Ruschinski & Retzlaff-Kresse 1974),我国曾参考这本书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翻译》(马克思、恩格斯 1978)。国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研究集中于对马克思翻译校对工作的梳理和介绍(Ertürk & Serin 2016)、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思考(Lezra 2018)、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策略的探讨(Carver 1997)。国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标准的讨论(林放 1983;陈德元 1987)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上的重要贡献(余士雄 1980)。本文对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典,系统整理了散见于马恩全集中有关翻译问题的全部论述,重点追溯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四大核心内容及三个形成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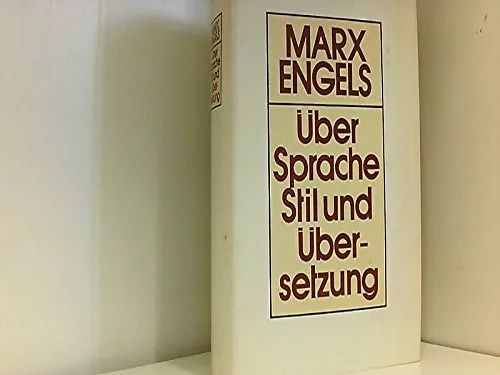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论语言、风格与翻译》
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哲学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理念由五个属性组成,它们相辅相成,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翻译的科学属性是统领性理念,奠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观的唯物主义基调;翻译的政治属性和传播属性是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活动的根本旨归,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观的革命性和实践性;翻译的认知属性和创造属性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译文凝结着对实践的认识,同时又对新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
1)翻译的科学属性。1885 年,恩格斯撰写了著名的《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强调翻译马克思著作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马克思、恩格斯 1965a:276)。为保证翻译的科学性,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翻译过程中的试译、转译、商译、审译、重译。如马克思在考察法文版《公社史》德译者时,“会寄几个印张给格龙齐希试译”(同上 1972c:188)。《资本论》的意大利文版是根据法文版转译的。恩格斯审校译稿时,用铅笔写上意见,与译者协商解决(余士雄 1980:21)。若译文质量太低,恩格斯会亲自重译,比如他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英译稿难译之处就重译了一遍。
2)翻译的政治属性。翻译的政治属性突出地表现在世界革命目标上。据马克思的女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P. Lafargue)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所述,马克思喜欢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马克思、恩格斯 1978: 221)。1872 年,马克思直接用法文写信给《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出版者:“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同上 1972a:26)。可见,教育启发工人阶级,推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合作,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翻译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3)翻译的传播属性。翻译是一种传播活动,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翻译工作的根本原因是向全世界传播其科学认识、政治思想和社会观点(施佩尔、金建 2011:4)。1885 年,恩格斯在与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贝克尔(J. Becker)通信时称:“要校阅大量的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丹麦文的译稿”,这证明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国际上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所以,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马克思、恩格斯 1974b:391-392)。
4)翻译的认知属性。翻译是马克思、恩格斯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工具。1852 年春,恩格斯与马克思通信时谈及他在学习俄语和斯拉夫语, 原因在于“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不久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同上 1973a:37)。可见,恩格斯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了解俄国和东欧国家国情并研判革命形势。同样,马克思 51 岁时学习俄语,是为了批判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 Bakunin),专门阅读其作品并择要翻译(同上 1978:163)。
5)翻译的创造属性。翻译之于原作是一种创造。1894 年,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女儿劳拉(Laura)对其著作的译文“读起来比原著还好”(同上 1974c: 225)。马克思审校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其译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原文。1873 年,恩格斯回信肯定马克思的译审:“我发现你加过工的确实比德文的好”(同上 1973b:105)。“加过工的”在原文中即为黑体,表明恩格斯强调译文质量的提高在于马克思翻译实践中的话语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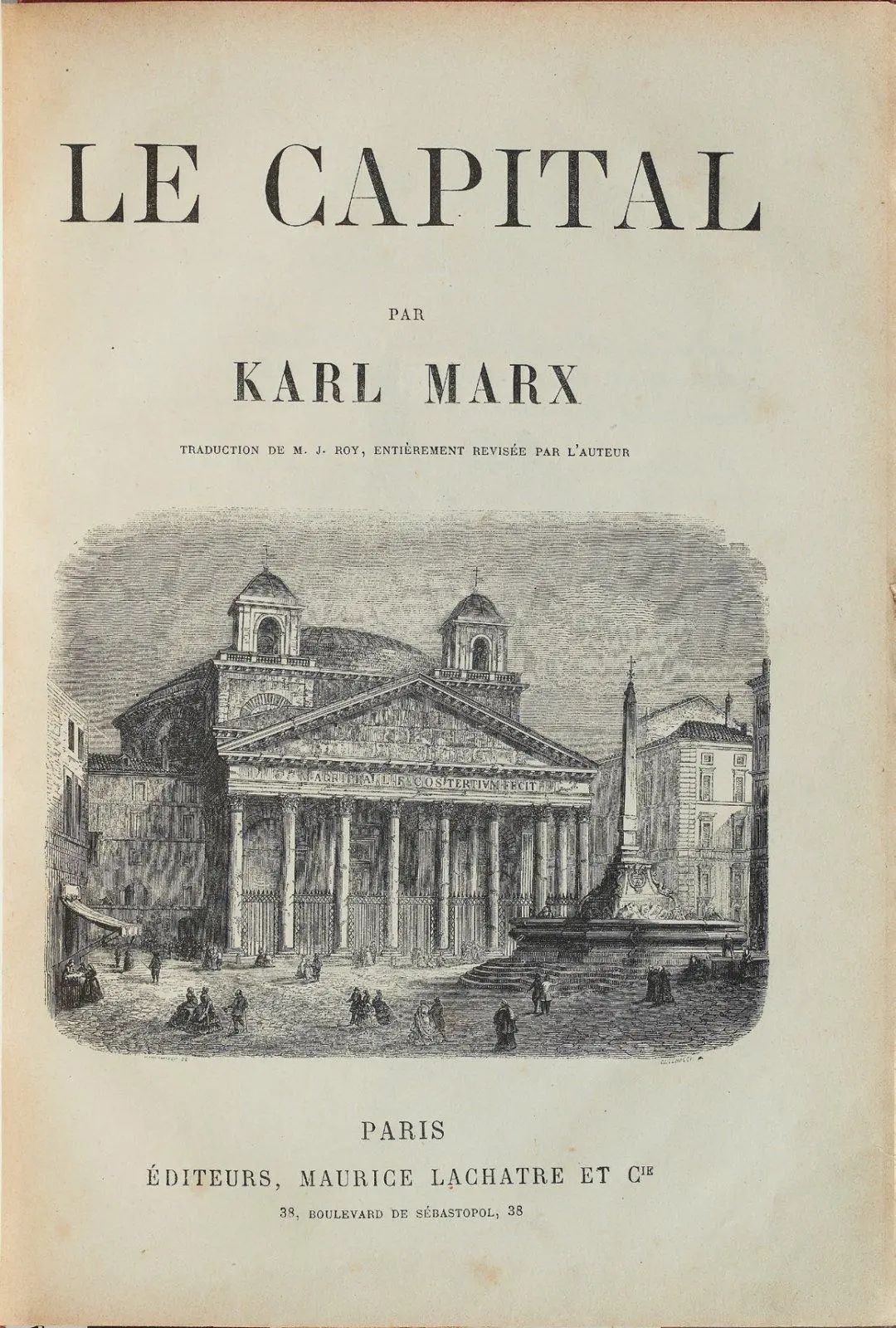
《资本论》法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译者的伦理要求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上,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译者的立场取决于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故而挑选政治忠诚的译者是政治文献翻译的必然选择。
第一,坚持政治忠诚。马克思指出,凡是为工人读者所写的著作,要“从译者必须是党员这一原则出发”(同上 1972c:205)。1867 年,马克思原本同意勒克律(E. Reclus)翻译《资本论》法文版,后了解到此人是巴枯宁的社会民主同盟成员,属于无政府主义者,便立即停止与其合作。马克思逝世后,克瓦尔克(M. Quarck)致信恩格斯,希望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法文版译为德文。恩格斯考虑到此人是保守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不能忠实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单继刚 2005:32)。
第二,恪守职业道德。1884 年,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论蒲鲁东》译为法文, 请劳拉与拉法格校阅,并强调“没有权利把马克思实际上没有说过的话强加于他”(马克思、恩格斯 1974b:128)。这就是说,译者要恪守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不得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或者故意增译、减译和改译。马克思阻止未加授权的《资本论》节译本发表,曾指出“未经我事先准许,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删节本的发行”(同上 1972c:139)。
第三,强化职业素养。恩格斯指出,译者必须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必须精通源语和目的语两门语言,“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同上 1965a: 267),还必须“具备用两种文字写作的经验”(同上 1974b:46)。除此之外,译者还必须精通专业领域。1893 年,在《资本论》意大利文版翻译之前,恩格斯提出“译者不但必须精通德文,而且还要精通政治经济学”(同上 1974c:80)。
第四,倡导语言多元平等。马克思、恩格斯尊重世界各国语言文化,曾称赞母语德语之外的多门语言,如称意大利语为“优美的语言”(同上 1971:366- 367),“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同上 1964:598)。恩格斯与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者通信时,经常使用对方的母语,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同上 1978:223)。1893 年,恩格斯为感谢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寄来的杂志,专门用保加利亚语书写“国际社会主义万岁!”,借此表明“已经开始懂得你们的语言”(同上 1965b:477-478)。
六大翻译原则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层面的翻译认知:一是在微观层面,忠实流畅(内容)、风格再现(文体)、活力等效(语用)、用语统一(形式)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观中语际转换的立体层次,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展现了语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和反作用; 二是在宏观层面,精神传播、受众理解才是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
1)忠实流畅。恩格斯在论述翻译问题时首先关注“忠实”原则。1885 年,恩格斯撰文批评了擅自翻译《资本论》的英译者,指出“译文远远没有忠实(treue Textwiedergabe)地表达原文”(Marx & Engels 1962:229;马克思、恩格斯 1965a:266)。此处德语形容词原形 treu 有两重涵义:“忠实”和“忠诚”。何谓“忠实、忠诚”? 1884 年,恩格斯在指导《论蒲鲁东》法译工作时称“请尽量更准确地表达原文”(马克思、恩格斯 1974b:129)。可见,“忠实、忠诚”的第一要义就是准确(genau)。1893 年,恩格斯在校对《资本论》意大利文版时,夸赞译者屠拉梯(F. Turati)“译文表达是相当忠实的(getreu)”(Marx & Engels 1968:94;马克思、恩格斯 1974c:92)。此处德语 getreu 的意思相当于英语a true copy 和 trusty,有“忠诚”之意。
要实现“忠实、忠诚”,必须确保译文流畅。1876 年,马克思在物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译者时谈到翻译“需要文字流畅生动”(Leichtigkeit und Gewandtheit)(Marx & Engels 1966:223;马克思、恩格斯 1972c:205)。1894 年,恩格斯赞扬劳拉对《费尔巴哈》的翻译“忠实而流畅”(马克思、恩格斯 1974c:190)。此处 “忠实”(gewissenhaft)指劳拉尽责对待翻译工作,而“流畅”(flott)实际上是恩格斯对译文质量的另一要求(Marx & Engels 1968:195)。恩格斯称劳拉已实现译文“读起来要像原著一样”的目标,这正是忠实流畅原则的最佳注解(马克思、恩格斯 1974c:83)。
2)风格再现。1885 年,恩格斯在劳拉进行《共产党宣言》法译工作时指出:“越是接近结尾部分(……)你就越来越不是翻译,而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了”(同上 1974b:361-362)。“用另一种语言再现”(in der anderen Sprache wiedergeben)(Marx & Engels 1979:370)对翻译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恩格斯强调“我们摹仿不了马克思的文体,但也必须使我们的文体不要同他的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 1974b:80)。此处“文体”的德语原文为 Stil,相当于英语的 style,译为“风格”或许更为恰当。语言再现的表征正是风格再现。
那么,翻译如何实现“风格再现”?恩格斯强调,除了词义还要注意句子结构和篇章风格。1847 年,马克思曾用法文写作《哲学的贫困》,后由伯恩斯坦(E. Bernstein)于 1884 年着手译回德文。恩格斯在与译者沟通时强调“您力求把意思译得忠实、确切,而有点忽视了文体”,应该“简化一下句子结构”(同上: 99)。另外,翻译之后必须统一全文的篇章风格。1886 年恩格斯校对《资本论》英译本时,要求修改过后必须“再通看一遍,从文体(stilistisch)和技术角度检查一下”(Marx & Engels 1979:473;马克思、恩格斯 1974b:464)。此处,德语 stilistisch 相当于英语 stylistic,指的正是文体和风格。
3)活力等效。1885 年,恩格斯在对《资本论》错误英译本的批判中,强调“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指出“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马克思、恩格斯 1965a:267)。在此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翻译原则——“富有表现力”。1873 年,恩格斯在与马克思的通信中也谈及语言的活力问题,恩格斯批评《资本论》法译本“力量、活 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同上 1973b:99- 100)。“力量”(Kraft)、“活力”(Saft)、“生命力”(Leben)此三力与“表现力”意义相同或相近,共同指向两种语言之间的活力等效,最终呈现的叙述面貌就是“鲜明性”(Frappante)和“生动性”(Lebendigkeit)(Marx & Engels 1976:94)。
可见,活力等效的首要特征是译作要传达原作鲜明的表现力。1889 年,恩格斯给劳拉写信称赞她的译文“非常接近原文的明快”(马克思、恩格斯 1971: 303)。再者,活力等效的另一维度是“生动”,比如 1883 年恩格斯曾表扬《资本论》英译者穆尔(S. Moore)的试译稿“译得很好、很活”(同上 1974b:64)。
4)精神传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了“交往” 概念,“精神交往”以“物质交往”为基础:“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同上 1960:29)。“精神交往”(der geistige Verkehr)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核心概念,指的是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郭庆光 1999:13-14)。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翻译本质上是两种文化思想精神之间的传播活动和交际行为,可以归纳为“精神传播”。恩格斯认为文字翻译应围绕精神实质展开,在谈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法译本时,他批评“腊韦和一切职业翻译一样,过分拘泥于原文”(马克思、恩格斯 1972d:60),并高度评价该书意大利文译者“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同上 1974b:316)。此处无疑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精神传播”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 1851 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道的:“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同上 196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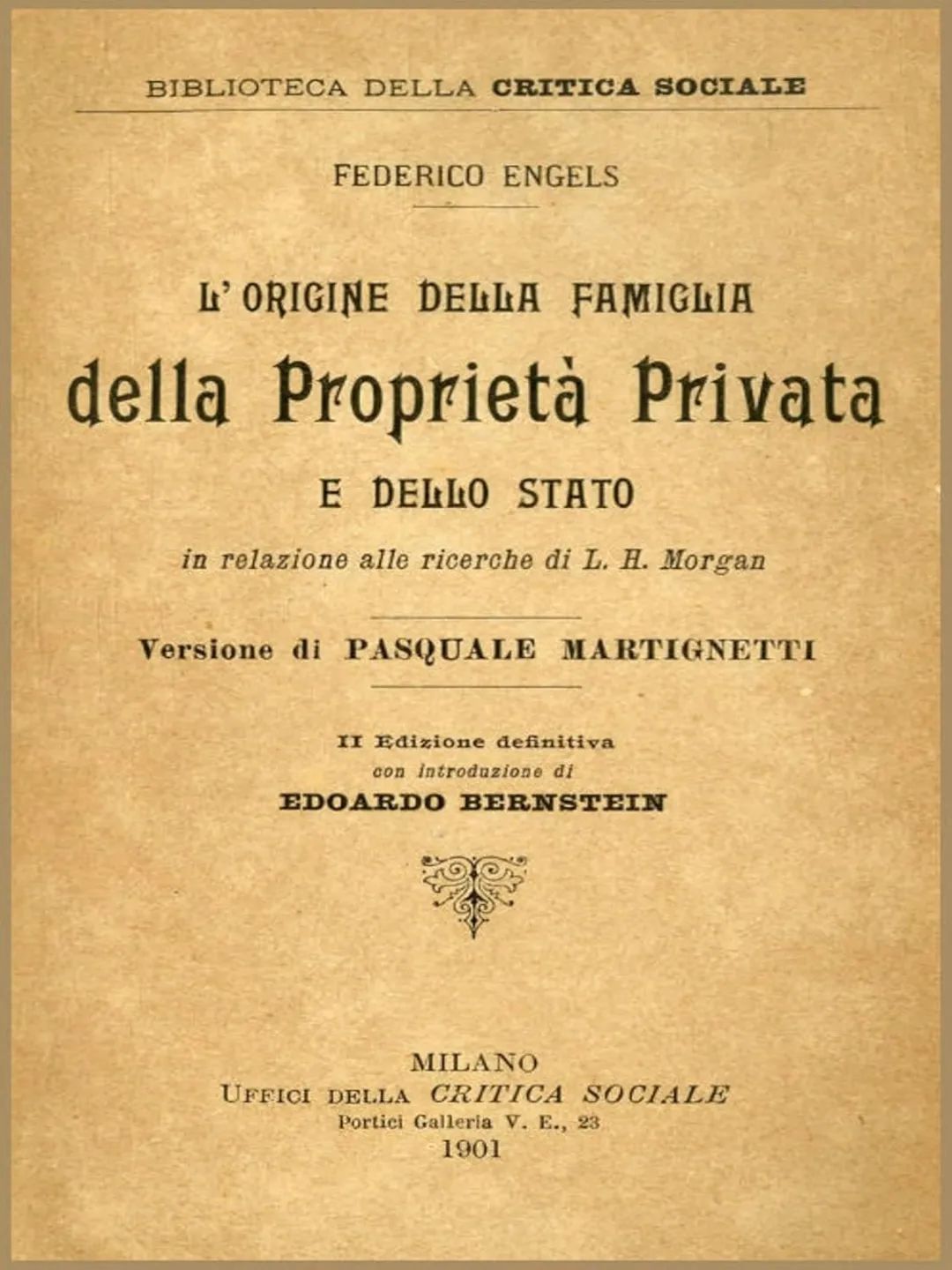
意大利语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5)受众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重视依照不同国别受众特点进行翻译。在1875 年《资本论》法文版序言里,马克思指出“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 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甚至马克思认为翻译活动中根据受众所做的改动可以反作用于原文的改进,比如《资本论》法文版“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因此 “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同上 1972a:29)。
恩格斯认为必要的翻译改写有助于增强传播效果。1887 年,恩格斯指出“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因此恩格斯建议将“《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同上 1974b:610-611)。翻译改写就是传递原著精神,其最终目的是扩大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力,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6)用语统一。恩格斯尤其重视翻译专门术语,实现译名统一和专业表述。1884 年,马克思以法文写作的《哲学的贫困》被译为德文时,恩格斯告诫译者“在德文本中,应当准确地沿用黑格尔的专门术语,不然就会不可理解”(同上: 138)。恩格斯高度重视翻译过程中译名统一校对工作,他在 1884 年《资本论》英译本统稿工作中强调“所有的译文都要经过我的手”,保持全文“用语的统一(在全书中用同一的专门用语)”(同上:141)。
马克思、恩格斯在翻译实践和译文审校中曾多次谈及翻译方法,形成了内涵丰富全面的翻译策略。他们的翻译实践是其翻译策略的直接来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特征。
1)造词译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善于“创造新词”,因此翻译时“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同上 1965a:266-267)。 比如,“交换关系”(Austauschverhältnis)是《资本论》里频繁出现的名词,德语 Austausch是“交换”的意思,而 Verhältnis 有“关系”和“比例”两个含义,英译者布罗德豪斯(J. Broadhouse)面对新词不加研究,将其译为 exchange-ratio,恩格斯则将其改译为 exchange-relation(同上 1965a:272)。
2)逐字译法。逐字译法适用于传递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重要的政治观点。1856 年,马克思用英文发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摘要引用了英国无署名出版的三本外交小册子,其中一本内附“逐字逐句的译文”(同上 1982:782)。恩格斯从葡萄牙《社会思想报》挑选文章译为法文时,专门提到葡萄牙语“几乎可以逐字逐句地翻译,所以我尽可能译得确切些”(同上 1973b:430)。
3)加注译法。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在译文中增加注释。1869 年,马克思在校对法文版《资本论》时,提醒译者“关于《Verwertung》〔‘价值增殖’〕一词(……)给法国读者加个注释”(同上 1974a:623)。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里摘录外交文本译文时大量作注,当时编辑认为评论不要用注释的形式, 而马克思认为很有必要,因为能够“提供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同上 1972b:522)。
4)删减译法。为了普及、传播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也会适当对原作做 些删减。1852 年,在恩格斯校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时,马克思直言“删掉不必要的辞藻和史实”(同上 1973a:143)。恩格斯在后期翻译中也注意到这一点,1872 年恩格斯物色《资本论》英译本出版者时,指出“为了适应这里的市场,应对这本书作较大的修改,删去引言中所有多余的话(……)并把晦涩难懂的文字改成通俗易懂的英语”(同上 1973b:483)。
5)改写译法。马克思、恩格斯既强调译文忠实和政治忠诚,也非常重视译文的受众效果和社会指涉。1872 年,马克思谈到《资本论》法文版的翻译时说: “虽然法文本(翻译费尔巴哈著作的鲁瓦先生的译本)是由精通两种语言的大行家翻译的,但是他往往译得过死。因此,我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同上:478)。
6)形象译法。1852 年,恩格斯在校对《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文时,指出不要用太多法语词源的词,抽象、不明确的含义会令英国读者难以理解,最好用形象译法:“凡是在原文中遇到生动的、具体的形象,差不多都可以找到萨克森语源中同样具体的、生动的表达法,使英国人一看就明白说的是什么”(同上 1973a:138)。
7)回译法。1886 年,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赞赏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Eleanor)“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同上 1972a:33)。1890 年,恩格斯在《资本论》英译版第四版序言中再次强调对引文进行全面校订的必要性,并肯定爱琳娜态度认真,“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同上:38)。
8)活译法。为了更好地传达原著的精神实质,马克思、恩格斯一贯注重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和表达方式。恩格斯曾充分肯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大利文译者,指出“许多地方,只要您很好地领会了意思,我认为您可以译得更灵活更大胆些”(同上 1974b:316)。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内在逻辑和形成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从翻译、校对、译审的实践经验出发,将译者、文本与受众紧密结合起来,关注从翻译选材、译文生产、译法选择到译文输出的全过程,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翻译理念,构建了系统完备的话语体系。其翻译理念、翻译伦理、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可谓四位一体:翻译哲学理念是其对翻译属性的深刻认识,翻译伦理以译者为中心,以受众为导向,架起文本内外之间的桥梁;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则由宏观向微观,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认知中的各个层面。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三个形成来源如下:
一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翻译实践、译文审校和外语习得。马克思、恩格斯皆掌握数门外语。马克思掌握英语、法语的说和写,能阅读几乎所有主要欧洲语言,并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恩格斯掌握大约二十门语言,其中十二门语言能主动运用。为了推进共产主义事业,马克思年过五十还决定学习俄语,以便更好地研究俄国的经济问题,进一步修订《资本论》中的土地问题。恩格斯在 72 岁时,为了向东欧和东南欧宣传社会主义,还在学习保加利亚语(Ruschinski & Retzlaff-Kresse 1974:14-15)。马克思审校过《资本论》法译本;恩格斯曾把马克思用英文撰写的《法兰西内战》译成德语,并校阅过《共产党宣言》的英、法、意、丹麦文译本等(余士雄 1980:21)。
二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语言的唯物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翻译观的基础。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 1960:525)。因此,语言和思想两者互相依存,具有同构性。同时,他们认为两者亦即语言与意识的关系,“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同上 1960:34)。
三是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政治和世界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历史的起点是近代国际关系的起点,而“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终将被共产主义时代所取代(柳瑟青 2007:55-56)。世界革命理论由此派生,其原因是单靠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陈宇、张新平 2017: 196)。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国际主义的”,要努力实现“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进而达到民族“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李爱华 2006: 48)。马克思、恩格斯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其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世界革命思想,促进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醒、相互了解和国际合作。

恩格斯故居中展出的《共产党宣言》译本
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由翻译理念、翻译伦理、翻译原则、翻译策略四部分构成,来源于翻译实践,并与其语言哲学和政治思想紧密相关。其中翻译理念和翻译伦理指向语言本体外研究,而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则属于语言本体内范畴,分别涉及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研究。
从翻译史角度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翻译思想并非沿袭德国 19 世纪翻译的“异化”传统。1813 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推崇忠实翻译,因为语言要表现“陌生的相似性”,使读者向作者靠近(Stolze 2011: 27)。与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虽秉持译文“忠实”观,但并非为了简单保留源语中的异质因素,而旨在切实传达源语文本的精神实质,同时亦非让读者向作者单向靠近,而强调作者/译者也可为读者在保留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改写内容。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受众理解和精神传播才是翻译的最终目的,因此其翻译观不仅仅囿于语言的理论层面,而是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其翻译思想的起始点皆落于实践,在于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指导全世界工人运动。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翻译理论的话语构建指向文本外的世界革命,内部理论与外部指涉辩证统一,再次凸显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践性。

时晓,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德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德语语言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德语近现代文学、外交话语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省厅级项目5项,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译著4部。


杨明星,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院院长,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译审。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及评审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特聘教授,省高层次领军人才,省管优秀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2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