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浩 | 倾诉的渴望——瓦肯罗德的语言批评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萌芽
本文原载于《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3年02期。感谢作者李晶浩老师和《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的支持。为方便阅读,本公众号不保留原文注释。


摘要 瓦肯罗德的《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开山之作。浪漫派文学独特的文学题材、艺术倾向和美学理论,在这本纤巧小书中已具雏形。作品对启蒙主义语言观的批评及对自然和艺术这两种“本真语言”的崇尚,源自诗人倾诉其宗教化艺术审美体验的强烈渴望。瓦肯罗德试图超越启蒙理性语言的限制,用诗意的言说去把握超乎尘世语言的“隐秘真理”,从而达到融入“无限”的理想境界。这正是浪漫派诗人的共同追求。
关键词 瓦肯罗德 语言批评 启蒙理性 浪漫派 自然 艺术


《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1797年出版于普鲁士的首都柏林。这本没有作者署名的雅致小书,“宛如整个浪漫主义文学建筑的基层结构”,“虽不是气势磅礴的创作”,其“萌芽能力却非常令人惊叹”(勃兰兑斯,104)。创作这部浪漫派奠基之作的,是一位热爱艺术、却迫于父命从事律师工作的二十三岁青年: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W.H.Wackenroder, 1773-1798)。瓦肯罗德在其作品中提出艺术创作启示说,将艺术审美体验比作虔诚的敬拜,使艺术上升至与宗教比肩的高度,因而被称作“艺术宗教”的开创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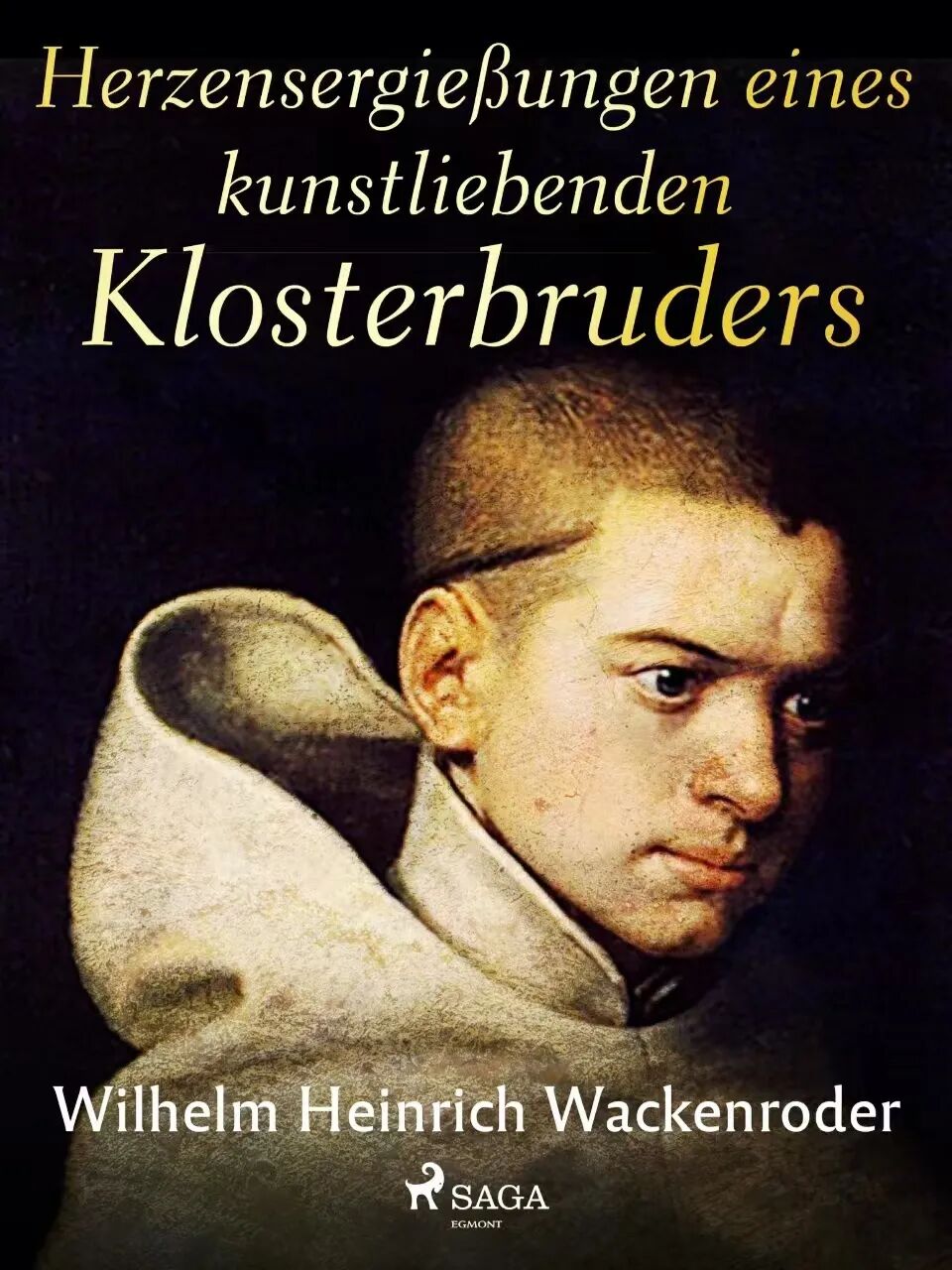
《一个热爱艺术的修士的内心倾诉》封面
瓦肯罗德倡导的这一“全新的艺术理念和美学主张”(Beutel, 227),与文集《倾诉》中贯穿始终的“语言隐喻”(Bartl,239)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批评在瓦肯罗德的文艺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倾诉》借一位热爱艺术的修士及音乐家伯灵格之口道出的语言观,体现了早期浪漫派对语言持否定态度的激进立场。瓦肯罗德及其同时代的浪漫派诗人对语言的怀疑和批判,与一个世纪后以《钱多斯致培根》为代表作的德语现代文学“语言危机”现象相比,尚有本质区别。作为启蒙思想的继承者和修正者(Bartl,240),瓦肯罗德的语言批评深受晚期启蒙语境中语言哲学和美学理念的影响。

威廉·海因里希·瓦肯罗德肖像,今藏普鲁士编年史档案馆
在《倾诉》之《论两种神奇的语言》中,瓦肯罗德以人类语言乃“上天的一个伟大恩赐”(倾诉,66)之论,加入到一场在启蒙的欧洲学界久盛不衰的、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论争之中。以基督教《圣经》为依据统治西方千余年的“语言神授论”,在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的18世纪,为愈来愈多思考语言哲学问题的学者所质疑。1769年,德国哲学家赫尔德 (Herder)以其论文《论语言的起源》,获得柏林科学院所设征求语言起源问题最佳解答的专项奖。赫尔德反对语言的超自然起源之说,提出“语言源于人类自身悟性”的观点,以“渐生说”(语言与悟性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而来)挑战科学院院士苏斯米希(Süßmilch)的“先成说”(语言乃悟性产生之先决条件)。启蒙学界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兴趣,来自语言在启蒙世界观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Kemper, 134)。赫尔德写道:“研究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认识人类努力进取的历史,探索我等理性诞生的奥秘,——有何使命比认识语言的起源与发展更高贵、更重要?语言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杰作,我对关于它‘童年时期’的哲学思考,有着浓厚兴趣!”(Herder, 62)显然,语言与作为启蒙哲学核心概念的“理性”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启蒙思想家莫里茨(Moritz)关于语言起源的立场(人的天性具有产生理性并创造语言的潜力),以及启蒙批判者哈曼(Hamann)的语言理论(语言兼具神性和人性,神圣的悟性降临在人性的语言中),皆体现这一启蒙学界无可争议的共识(Kemper,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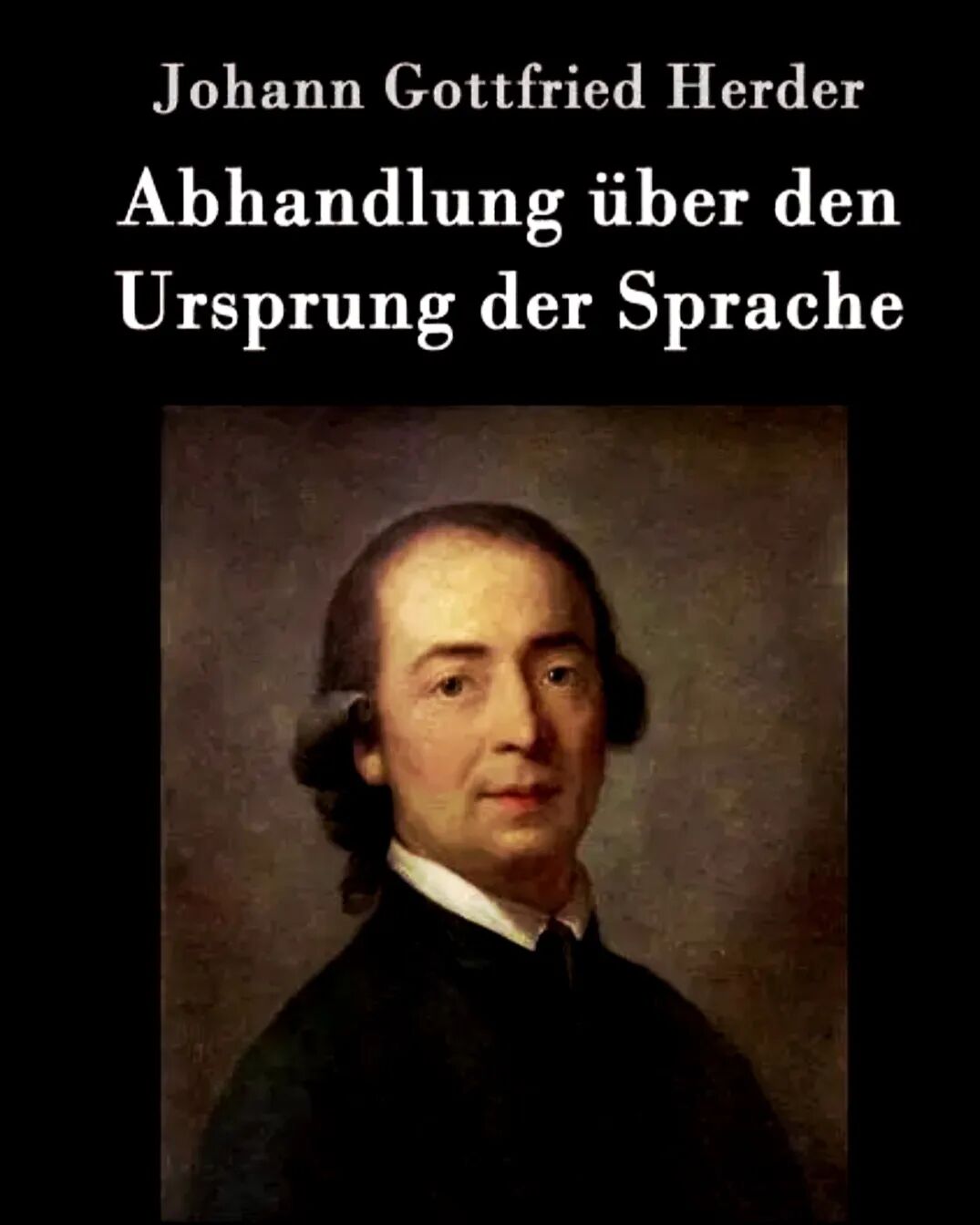
赫尔曼的柏林科学院获奖征文《论语言的起源》
如果说,“语言渐生说”的支持者认为语言与悟性互相更新、不断发展,体现的是相信理性不断进步、完善的乐观启蒙主义,那么,瓦肯罗德强调语言为神所赐,支持苏斯米希关于理性源自语言的“语言先成说”,是否同样在为理性辩护?——既然语言来自神完美的创造,理性产生于语言则亦必完美。初看之下,瓦肯罗德重提“语言神授论”,似乎并未让他站到启蒙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其实不然。在《论两种神奇的语言》中,瓦肯罗德对人类命名万物的理性活动和为人类所独有的理性语言本身,做出了明确的批评。
“通过话语我们统治着整个世界,通过话语我们轻而易举地获得地球上所有的宝藏”(倾诉,66)——人类通过命名万物获得造物中的特权地位,在道出世间万物名字的同时,也将它们攫取并占有。“地球上所有的宝藏”能为人所获取,“天上的财宝”却是囿于“此在”的世人所无法触及的。与《圣经•马太福音》中对世人因乐衷于“积累财宝在地上”而失去“天上宝藏”的警告相呼应,瓦肯罗德对人类乐衷于用理性统治世界、自恃能用理性的语词语言去认识一切、却无法认识天上的“隐秘真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独具语言能力的人类之自大与谬误的批判,完全符合瓦肯罗德反启蒙理性主义的立场。
赞同哈曼“语言兼具神性与人性”观点的瓦肯罗德认为,“语言具有人性”是更应突出的一方面。语言具有人性,意味着语言受到人性或曰人类理性的局限,语言囿于其理性本质和“此在”特征(Dill, 66)。在对人类“通过话语”获取“地球上所有宝藏”的批判中,理性语词语言的界限凸显出来:它所指陈的事物是具体的,它的使用范围局限于世间的、人类感官可感知的事物上。根据《圣经•创世记》,掌握了语词语言的人类,被神赋予的任务与特权,乃是“治理这地”——理性语词语言的有效范围,早已限定为这个有形的世界。而“飘忽于我们之上的那些无形的东西,语言无法将其引入我们心中”(倾诉,66)。瓦肯罗德断言:语词语言作为有形与有限的此世事物的象征符号,无法涉足无形与无限的彼岸神圣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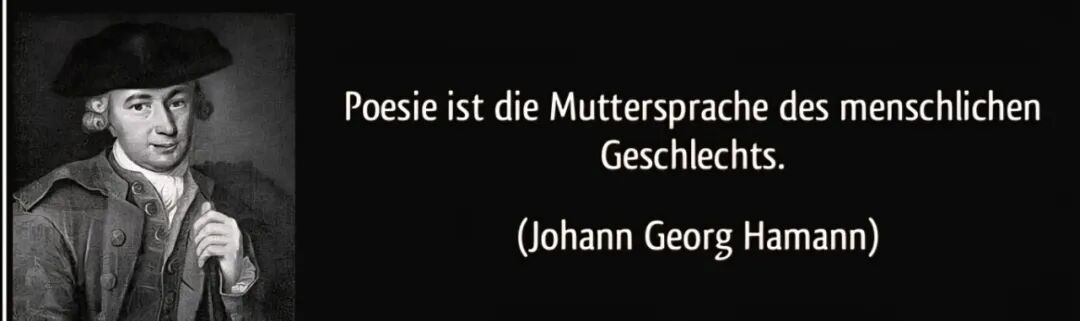
哈曼的语言理论:语言兼具神性与人性,诗歌是人类的母语。
倘若用理性的语词语言谈论“上帝无所不在的恩泽”,诉说“圣贤们的美德”,聆听者耳中充塞的将是“空洞无物的轰鸣”,他们的精神无法变得“庄严和崇高”(倾诉,66)。相反,盛大华美而又庄严肃穆的天主教弥撒,无需理性思辨和逻辑语言,却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使他的灵魂飞至云霄,让彼岸的神圣世界向人敞开怀抱。在瓦肯罗德那里,强调理性语言局限性的直接后果,即是让依赖于语言文字、以阐释“圣言”为核心、因而被称为“话语宗教”或“理性宗教”的新教,让位于将理性语言消解、由感官体验主导、被称为“感性宗教”的天主教(Wiese,278)。瓦肯罗德在《倾诉》中第一次以文学形式描写的新教徒画家皈依天主教的经历,成为后来大批浪漫诗人皈依天主教的榜样(谷裕,255)。
瓦肯罗德亲身体会到,天主教盛大仪式所唤起的心灵中对圣洁与虔诚的渴望,无法用理性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以理性语言为媒介对虔信的呼唤,则必然同样只能向人的理性说话,而无法触动人的心灵。“智者的教诲只能打动我们的头脑,也就是说,它只能打动我们一半的自我”(倾诉,69)。对瓦肯罗德影响颇深的哈曼在其《论美学》中亦指出,较之艺术,语言的功效仅限于人的理智,它不能使“全人”受震撼(Müller, 231)。在批评语言这一缺陷的同时,瓦肯罗德提出了与理性语言“迥异”的两种“本真的语言”:自然和艺术。自然和艺术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既可以打动我们的感官,又可以打动我们的精神”,教我们“通过这两重道路”去认识“上天的奇迹”(倾诉,69)。
感官和精神,或曰感性和知性,是实现认识的两重道路。瓦肯罗德此论继承了康德对“两大主干”理论的思考,并对其在《纯粹理性批评》中“轻感性,重知性”的立场提出了批评。与康德的批判者赫尔德的观点相似,瓦肯罗德认为,感性不仅与知性同样重要,更是达到深刻认知的直接途径。自然和艺术之所长就在于,它们提供了语词语言所缺乏的直接的感官观照,这种观照对人获得深入的知识和深刻的体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Bartl, 154)。瓦肯罗德相信,在观照大自然和艺术作品的动人画面时,人的心性,即感性和知性的结合体,将以奇妙的方式受到触动,正如启蒙美学家莫里茨所言:“当我们看到美的事物时,我们感到我们的心灵和理智都得到了拓宽。”(Moritz, 96)
两种“神奇的语言”之一,“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大自然,是造物主彰显其神性的奥秘之语。瓦肯罗德笔下的修士感叹道:“一段优美的山谷,为许多千奇百怪的岩石所环绕,或是一条平静的河流,其中倒映着婀娜的树姿,或是一片开阔的绿色草坪,映照在蓝天之下”,所有这些事物,“都比任何话语更能神奇地触动我内在的情怀,更能深刻地把上帝万能的力量和他万有的恩泽载入我的精神,更能使我的灵魂变得纯洁和高贵!”(倾诉,67)。修士承认,“少年时代的我”曾通过“古老的圣书”认识人类的上帝,“而时至今日”,他终于明白,“自然”才是一部解释上帝的本质与特性的最全面、最明了的书。”(倾诉,69)瓦肯罗德将依赖于语言文字的《圣经》与大自然的“无字书”作对比,明确指出大自然这部“清楚的解释之书”,乃是优于《圣经》这一“晦暗的谜语之书”的更可靠、更直接的启示之源。与之相应,话语和文字与自然之语相比,“不过是一种尘世的、简陋的工具”(倾诉,68)。借助语词语言这一“简陋工具”既无法认识上帝之道,对上帝的体认之关键,便从聆听和阅读“古老的圣书”之言,变成了目睹大自然之壮美的审美体验(Neumann,167)。瓦肯罗德将本真的自然之语视为真正启示之源的理念,影响了早期浪漫派诗人崇尚自然、歌颂自然之美的艺术倾向。
提供更神秘、更丰富的审美体验的艺术,是瓦肯罗德推崇的另一“神奇的语言”。艺术“通过人类中的图像说话”,能以“动人而奇妙的方式”,将不可见的、无限的精神“融化到可见的形体之中”,使观看者在看到局部的、熟悉的形象符号时,产生整体的、神秘的联想,使其“整个身心为之震撼”(倾诉,72)。瓦肯罗德将艺术的语言比作古埃及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en)。这种未经理性翻译的秘密符号,外形能被人观察和研究,其涵义却神秘莫测,无法轻易破解。瓦肯罗德认为,语词语言的语音符号和文字符号,一旦其意义被破解,便成为可以“弃之身后”的“无用的外壳”,人们探究其义的“精神劳作也随之停止” (倾诉,79)。而以“精美的绘画”为代表的艺术则不同,它那宏伟瑰丽、变幻无穷的图像所蕴藏的涵义,远非人们“费一时之力”所能掌握:“它带给人的享受是持续的,永不磨灭的。我们常常以为早已透彻地理解了它,而事实上,它却总是不断点燃我们新的感受,我们心灵的感悟永无止境。”(倾诉,81)
艺术作为有着具体形象的符号语言,比语词语言抽象的概念式语言,更能予观赏者以生动鲜活的印象,给人的心灵带来无穷的感悟。瓦肯罗德借修士之口承认道:“基督受难的画面,圣母像或圣徒群像,我敢说,它们比道德的体系和神学的思辨更能净化我的情感,更能在我的内心注入神圣美德的良知”;“壮美无比”的圣·塞巴斯蒂安像,令修士产生“强烈而深刻的基督教情感”(倾诉,79),远胜过抽象的文字和言语。在《画家编年史》一文中,瓦肯罗德用卡拉奇兄弟分别以口述和绘画再现伟大的雕塑“拉奥孔群像”的尝试,证明在表现壮美形象时,直观的艺术比抽象的语言更胜一筹。
对瓦肯罗德来说,语言在艺术面前的弱势地位,还表现在它无法恰如其分地描绘艺术作品之“美”这一缺憾上。在《对两幅画的描述》一文中,瓦肯罗德首先对能否用语言描述绘画之美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我认为,一幅美的绘画作品其实是不能用语言描述的”,因为“一说到‘美’以外的词”,一开始对画的各个部分做具体的描述,“人们对画的想象就会烟消云散”(倾诉,42);无论是达芬奇作品中的“美妙和精彩”,还是拉斐尔作品中“闪烁神圣光芒的妙处”,热爱艺术的修士都“完全无法用语言描述”(倾诉,42)。莫里茨则在《美的表记》中指出,艺术作品根本毋需用语言去描述,因为语言的描述永远不能反映作品真实的“美”,反而将作品歪曲,以至于语言信息的接受者不可避免地对“美”产生完全错误的想象。《倾诉》中的《老画家之死》一文,即是对莫里茨这一美学思想的生动阐释:老画家弗朗西亚从未见过拉斐尔的作品,却基于一些完全无法再现拉斐尔之精湛画技的描述,骄傲地确信自己的作品绝不逊色于拉斐尔的杰作。一直被语言“欺骗”的老画家,在亲眼目睹拉斐尔的油画《圣西西里亚》时,万分震惊以至羞愧而死。瓦肯罗德用这一不可思议的故事,形象地指出了语言在描述艺术作品时难以避免的偏差,提醒人们认识“语言具有欺骗性”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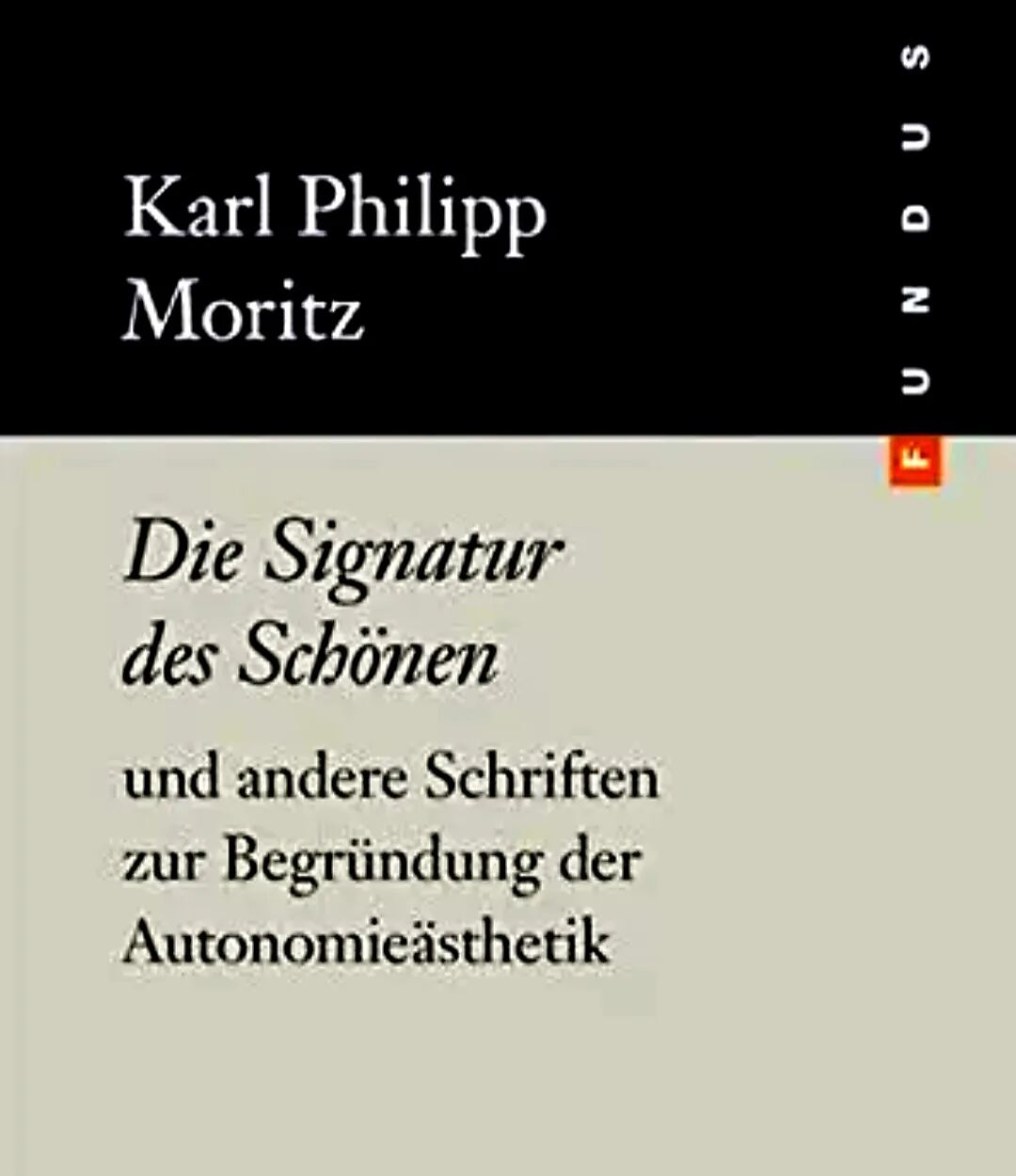
莫里茨《美的表记》封面
语言既不能反映艺术之美的真相,用科学术语式、分析定性式的理性语言作艺术批评,更是瓦肯罗德强烈反对的做法。《拉斐尔的显现》一文批评以理性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作艺术评论的那些“所谓的学者或理论家们”,认为这些“自作聪明的文人”在用“虚荣的、俗不可耐的伪哲理”令人不知所云地解释艺术作品,“喋喋不休地”讨论艺术精神和艺术美的本质,却对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一无所知”(倾诉,31)。赫尔德亦反对以工具性语言做系统化艺术评论,他认为,取得了美学独立性的艺术有其个性,非理性体系的普遍标准所能衡量和评价。对瓦肯罗德来说,更重要的则是:艺术作品的美和其中隐秘的神性,具有本质上的不可言说性(Bartl,259)。
《倾诉》中贯穿始终的话题之一即是语言与艺术图像之间的关系。早期浪漫派诗人对语言的反思,一定程度上始于对“艺术图像的不可描述性”问题的探讨(Bartl, 157)。莫里茨的“图像无法通过语言再现”的艺术理论,以及保罗的“精意与字句”二元论,皆深刻影响瓦肯罗德对话语的局限性及艺术精神“不可言传性”的思考。瓦肯罗德认为,艺术是表达神性精神的语言,它和“象形文字”一样,借助神秘的图像,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建立联系。艺术图像那感官的、有限的符号指向超感官的、无限的精神,可见的人性艺术指向不可见的神性世界。“字句”所(无法)传达的“精意”即指此“不可言说”的神性世界。
瓦肯罗德将神学来源的“不可言说性”运用到完美的艺术作品上,使其成为无法言说的对象,只能观照而不可言说。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尔(K.W.F Schlegel)亦认为,那“至高者”不可言说,仅以“现象”予人启示,让人用心灵的眼睛去观照(Schmitz-Emans, 298)。浪漫派作家霍夫曼(E.T.A.Hoffmann)同样论及艺术中非目睹所能及的“永恒精神”:“真正的艺术是在可见之物的彼岸”(Bartl,257)。在《倾诉》中,当瓦肯罗德笔下的青年画家“定睛”观看拉斐尔的作品,“那些色彩丰富的人物”便从他眼前渐次消隐,只剩下“空空如也的画板”;此时,他已“怀着最强烈的爱”,将他的心灵献给了无法言说的“美”——“那些天上的但同时又是人间的形象”(倾诉,93)。
莫里茨将“美”定义为“于自身中完善者”。这一源自“神人同形说”的定义启发了瓦肯罗德:艺术应展示与造物主的意旨相符的完善者之内在神性(Arendt, 176)。在瓦肯罗德眼中,“艺术为我们塑造了人类至高的完美”,对艺术的“充满爱”的、毋需言语的观照,能够“向我们开启人类心中的宝藏,将我们的目光引向我们的内在,向我们展示那些无形的东西,即人的形体中所蕴含的所有那些高贵、崇高和神性的东西。”(倾诉,53)艺术以无与伦比的方式激发人们对不可见的神性世界的无穷向往,它是仅为获得启示的少数人开启的、通向天堂的道路。惟有为上天所特选的精英,才能理解艺术,并通过艺术去表现神性。瓦肯罗德认为,艺术是神性在人类创造活动之中的彰显,亦是人向造物主敬献的宝物。人透过艺术去瞻仰和体认造物主的奇妙和伟大,艺术构筑了人敬拜上帝的圣坛。
当瓦肯罗德通过艺术这一神性的语言,得以“认识和理解一切事物的真正精神”(畅想曲,261),并在对至善至美的诚挚追求中,向那至圣至高者奉献自己的身心之时,他的心中便无产生了要将其所感、所思与所得予以言表的强烈渴望。将他对崇高的无限向往、他在艺术观照中所获精神的升华、他在艺术的圣坛上所体验的有限与无限的相交,向善感的心灵倾诉——这一至诚的渴望是瓦肯罗德文学激情的源泉,亦是早期浪漫派文学的精神动力。
然而,瓦肯罗德和他笔下所有的艺术之友一样,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痛苦挣扎:必须用话语去传达一种无法用话语传达的感性经验。青年画家安东尼在观赏拉斐尔的作品时,灵魂经历了一次“奇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跃”,但他却无法用语言向他最亲密的朋友表达自己的感受;他唯一的渴求便是:“惟愿你在我身边,让我握住你的手,将它放到我跳动的心上!”(倾诉,98)音乐家伯灵格在雄浑、悠扬、“宛如一道劲风从天而降”的音乐声中,内心喷涌出一种又悲又喜、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多么想让“身边聚集的不和谐的心灵”,感受到在他内心奔腾的激情,听到他对神圣的音乐艺术的盛赞!深知凡俗语言无法奏效的伯灵格,惟有求助于“天使的语言”——音乐:“音符啊,快来救我吧,脱离这痛苦的、在凡俗语言中的挣扎!”(倾诉,330)
在《音乐艺术的真谛》一文里,瓦肯罗德道出了音乐那使人心灵得自由的伟大力量:“当我们心中那火焰般的热情、极乐的颤栗、狂喜的风暴、使人热血沸腾的崇拜,将语词语言——这个内心激情的坟墓,以一声高呼冲破时”,音乐便在“崭新的天空下,在极乐的琴弦震动中,以宛如彼岸生命的美妙无比的天使形象”(畅想曲,326)获得重生。音乐中那一种“古老的语言”复活了,“那是我们的灵魂曾经懂得,将来必重新习练的语言”(畅想曲,343)。这种惟一能将人从语词语言的坟墓中释放出来的语言,即是来自心灵的、与音符相似的语言。
瓦肯罗德在将音乐视为“灵魂之语”的同时,亦提出将语言音乐化的诗学要求。语言应像音乐那样,更有韵律,更形象化,更富想象力,能使人的心灵充盈,表达浪漫的遐思,带给人精神与灵魂层面的享受。莫里茨认为,诗歌的语言是人类语言中与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最相似的语言,它不像科学的理性语言那样条分缕析,而是从整体上综合融会一切感性的力量,全面地作用于人的心性。瓦肯罗德赞同莫里茨的美学与诗学思想:只有在客观现实让位给诗意的描绘之时,美留在人们想象力中的痕迹才能重新化身为美(Zürner, 145)。瓦肯罗德指出:“一旦描述变得真正富有诗意,它就能使一切变得明澈,它在图像中唤起一种活泼的喜悦,一种欢快的理解,其效果宛如音乐,但却用闪亮的意象代替了与之有着亲缘关系的音符。”(畅想曲,322)如果说,就形式而言,富有韵律的诗歌语言与音乐的效果相似,适于描绘感性经验,那么,诗歌的本质更赋予了诗化语言一种能力,使其将艺术中不可言说的神圣光芒展现出来。
浪漫派文艺理论家小施莱格尔(A.W.Schlegel)认为:“所有的美都是隐喻式的。那至高者,因其不可言传性,只能用隐喻道出。”(Neumann, 98)诗歌的本质即是隐喻,它借助想象和象征追求并表达无限和永恒的精神,将形式的完美与精神的升华融为一体。对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来说,诗歌具有一种神秘的特质:“它展示那不可展示的,观察那不可显露、不可感知的。”(Wiese, 130)在瓦肯罗德那里,不可见的精神是可见的图像之真谛,而诗歌的语言则具触及并穿透那不可见的精神图像的能力,诗歌可谓一把开启那不可见的彼岸世界的钥匙。在《倾诉》中,每当年轻敏感的“我”在鬼斧神工的大自然、精美绝伦的艺术作品、夺人魂魄的音乐中瞥见“天上的宝藏”、获得妙不可言的感悟,敛声屏息而又心潮澎湃之时,诗意的言说便喷薄而出。
然而,对音乐化的诗歌语言推崇备至的瓦肯罗德却没有留下大量诗歌作品。究其原因,仍与他的语言怀疑论有关。瓦肯罗德在肯定诗人于“受到启示的瞬间”,能用诗意的言说称谓神圣之美后,却承认道:“我们[...]终不能将其融入语言之中。”(倾诉,53)在瓦肯罗德看来,语言努力靠近那不可见、不可言说的崇高境界,却永远不可能真正触摸到它的神圣本质。诗意的文学语言在一条神秘的、向着幽远的高处无限延伸的阶梯上奋力攀登。这一认识与小施莱格尔关于浪漫诗是无限的、无止境的基本观点正相契合。施莱格尔兄弟在《雅典娜神殿》里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定义——“渐进的万象诗”(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之诸多特征,在瓦肯罗德的文集《倾诉》里已有显著体现。
《倾诉》的体裁和文学手段多种多样,形成一个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整体。散文随笔、奇闻轶事、抒情诗歌、由对话和独白构成的微型戏剧、将各类文体融于一炉的小说等等,在瓦肯罗德的作品中以界线分明的断片的形式被组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的文体风格呈现出开放性和延伸性,共同指向理想的文学形式。同时,以断片为特征的文本明白无误地提醒读者,依赖于语言文字的作品具有暂时性和有限性,促使读者去认识世间语言的缺陷,并检验自己与语言这一人们赖以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之间的关系。
瓦肯罗德作为诗人的短暂人生、其天主教情结、对文艺复兴时期和中世纪艺术的崇尚,以及用感性的诗意语言代替理性的世俗语言的尝试,均给予早期浪漫派的文学与美学诉求以决定性的启迪,正如丹麦著名文艺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言:“他的一生有如一阵柔和的微风,在初春的日子里使空气变得温暖起来,从而诱发第一批花朵开放。”(勃兰兑斯,125)而瓦肯罗德的“艺术宗教”和他的语言批评,则可用他在《倾诉》中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来总结:“普遍的、本原的美,我们凡人只能接受神的启示去观看它,并在那受到启示的瞬间去称谓它,然而却终不能将其融入语言之中。”

李晶浩,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德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思想史、德国文学与圣经文学传统、西方翻译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