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贺询《德意志古典艺术(1755—1832)》

《德意志古典艺术(1755-1832)》
贺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6月
点击图片,购买本书
德国艺术史、思想史领域常把1755年(温克尔曼发表《关于在绘画和雕刻中摹仿希腊作品的一些意见》)到1832年(歌德逝世)之间的历史阶段称为“古典艺术时期”,用以概括当时文化界以古希腊、罗马为榜样,重新挖掘古典时代风格和文化价值的倾向。对其的探讨成为当今国际艺术史、艺术理论学科的重要基础和传统来源。
本书结合大量一手文献,全面追溯与深入剖析此阶段德意志古典主义艺术思想及其艺术实践,并兼顾当代艺术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一话题上的新进展, 挖掘古典艺术理论在当今世界的脉延, 在文明互鉴的意义上为艺术学研究提供养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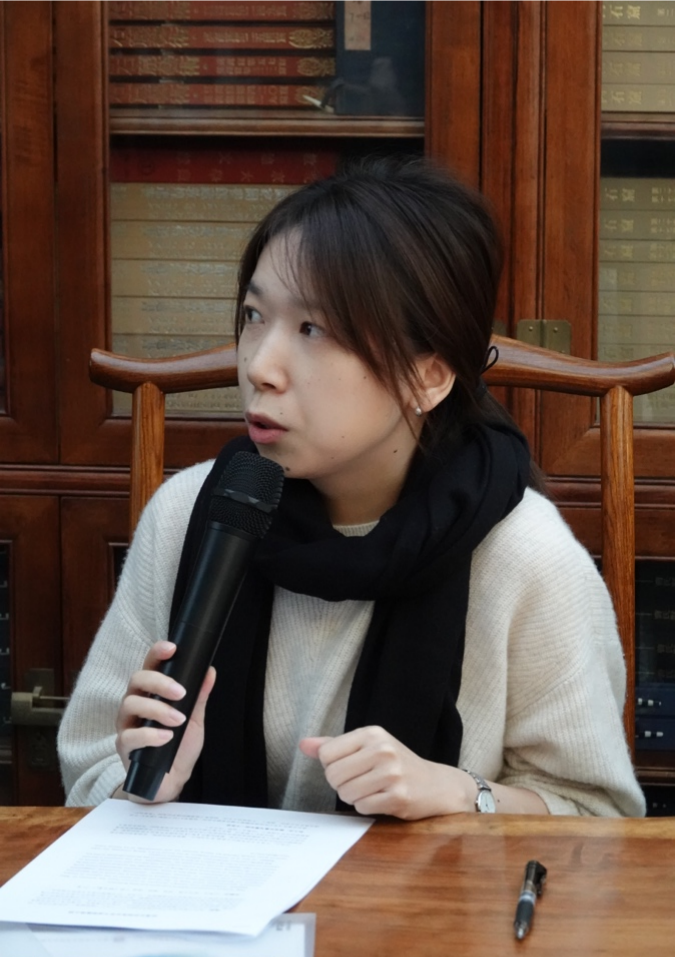
贺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艺术与美学、艺术理论、艺术史研究方法等。出版有专著《拉奥孔经典论争及其在同时代艺术创作中的影响:1755—1872》(慕尼黑大学),《德意志古典艺术(1755-1832)》(北京大学出版社),译著《艺术史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1 绪论
3 现状与视野
8 德意志民族艺术传统与古典艺术的交汇
27 上编: 古典艺术的理念
29 温克尔曼与《拉奥孔群雕》
67 “虚假激情”: 关于西方古典雕塑的一个辩题
81 希腊艺术风格分期与作品
107 莱辛的诗画分界说
129 魏玛的理念与实践
142 外延: 古典与异教
169 下编: 艺术创作中的反映
171 大众视野中的古典艺术
191 夸张变形的古典艺术
209 自然科学中的古典艺术
232 浪漫之潮: “从古典中诞生的浪漫”
270 参考文献
291 索引
307 后记
德意志民族艺术传统与古典艺术的交汇
艺术之所以诞生, 根源在于人类文明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在这个过程中, 艺术家, 也即有创造力的人类代表, 模仿自然宇宙造物时的“形态法则” (Formgesetz) 创造出了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各种作品, 风格的概念也脱胎于其中。基于以上观念的启发, 风格分析的大师李格尔提出了“艺术意志” (Kunstwollen) 的概念。艺术从诞生之初, 便肩负着与易逝的自然相竞技的使命, 具有自我的生命。李格尔尝试从同时兼有秩序与混沌、注定与偶然的艺术历史洪流中, 发现一条具备自身意志的发展主脉络, 认为艺术的发展甚至不必然贴合于历史现实, 显现出趋同、对抗、争锋、空想等形形色色的形态。其观点虽然按照现代的史学观念, 不乏对复杂历史人格化、浪漫化的想象因素, 但也开启了学者不断从艺术的反映中把握自然、地域、时代、民族面貌的道路。古典艺术作为一条忽明忽暗的线索, 始终穿插在德意志民族艺术发展的过程中。
关于德意志民族艺术传统究竟何为的讨论, 历经数代学者的接续探索。威廉·品德尔(Wilhelm Pinder) 作为早期关注德意志民族艺术的学者代表, 其重要专著《诺曼底地区罗马式室内装饰调性的初步调查》(1904 年)和《维尔茨堡的中世纪雕塑》(1911 年) 均从地方性本土艺术现象入手。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所作的《美术史的基本概念》(1915 年) 在欧洲文明的视角中, 观察古典艺术过渡到近代所发生的偏移。他精确抓取的“线描” 概念尤其具有北方所流行的版画艺术与勾勒技法的特质。随瓦尔堡学派迁居英国的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 则在《形象的遗产》(1970 年) 中, 更加笼统地讨论了历史的“形象语言”, 探索神话与宗教叙事中唯有诉诸形象才可以传达之物。之后, 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 的著作《德国人和他们的艺术》(1992 年) 再次总结了20 世纪时对德意志民族艺术的观感, 尤其引入战后的反思视角。



图书内页速览
无论学者研究的兴味在于大千世界中无限丰富的形与象, 摸索其衍生出的线条、色彩、团块、构图、造型, 还是回溯时光, 探索那些有信仰、有追求、爱梦想之人所塑造出的形象之意, 归根结底, 艺术造物从自然与人力中凝结而出, 在漫漶不清的历史洪流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鲜明特征。正是这些鲜明的特征, 勾勒出了“民族” 这一概念的具体形象。回溯德意志民族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特征鲜明的数个阶段。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 关于古典艺术的讨论在18 世纪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高光。
伴随着古典世界的彻底失落, 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也同时成为各地域性民族乃至国家逐渐成形的历史。一神论作为古典世界多神论的后继者, 更加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描绘, 因为自然界显现的是有限与易逝之物, 而灵魂之美远超实体之上。其本质上反映的是, 基督教出现后逐渐形成的一种中世纪超验世界观的图景。虽有罗马文明的外部冲击, “未开化” 的日耳曼人还是发展出了颇具民族特质的自然观。在查理曼(Charlemagne) 引领的“文艺复兴” 潮流之下, 艺术的教育与智性的教育、灵性的修养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样一种宏大的艺术图景中, 古典艺术的因素自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伊始, 实际上从未完全消逝, 形成所谓的真空一般的“中间时期”: 古典时代遗留下的废墟、遗址、绘画、雕塑和各类宝石、徽章,影响了查理曼加洛林时代的造物, 以及之后的罗马式建筑和文艺复兴。尤其古罗马文化艺术的遗风影响颇深, 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中反映为帝国愿景和基督教世界观的融合。一方面, 加洛林艺术的思想框架在于复兴古典时代的艺术, 因为它一定程度上是复兴罗马帝国政治愿景的衍生品。 查理曼的行宫亚琛皇城(Aachener Königspfalz) 集艺术作坊、文教团体、宗教机构于一体, 为欧洲宫廷树立了标杆, 成为一个比肩于古罗马和拜占庭皇宫的缪斯之家。无论亚琛皇城中的八角形教堂、《皇家福音书》, 还是各色圣物器具, 都显示出宏伟、精致而绚丽的宫廷艺术风格。另一方面, 加洛林-奥托艺术中发展出了着力描摹本地自然风土的精妙风格, 其中最能反映其美感质地的是由缠结条纹(Bandverschlingung) 构成的各种拟生化的形象(图1)。这些图案从早期的金银线和金属花丝风格装饰中脱胎而来, 演变成600 多种抽象动物风格的缠结纹样。这些形态各异、或善或恶的兽形纹样, 绵密地铺满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绘画中的平面空间, 形成一种精巧灵动、富于寓意的图样。人们用古已有之的“留白恐惧” (horror vacui) 概念来描述那种填满并去除所有空白的内心追求。它在这一类诠释灵性智慧的图像中, 无限强化了装饰之繁复的倾向, 使装饰本身转化为艺术。而备受教会与宫廷推崇的拜占庭风格, 发展出了细密画变体: 以精巧的形式显现于案头纸上, 且充满文气。
抽象化、平面化, 具有朦胧美感和精细几何造型的图像早在拜占庭帝国时代就已十分丰富。它们逐渐背离了古典时代壁画与雕塑中那种生机盎然、充满鲜活个性的描绘方式, 不再热衷于仔细描摹那些优美的人体、鲜美的花卉、多姿的动物, 乃至一切直观的世界。对自然比例的违背和对透视的颠覆等, 都是出于这种原因。扁平而抽象的精妙纹样大量堆叠, 象征手法大行其道, 营造出一种有距离感的、非现实的图案艺术。尽管它们同样达到了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 但其道路已背弃了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精神,不再关心世俗生活, 而转向精神生活中的思想与理念。
这一时期, 修道院成为存在于宫廷艺术作坊之外的另一大艺术生产地。赖兴瑙岛上的三座本笃会的罗马式教堂, 或称赖希瑙修道院(Kloster und Münster Reichenau) 精确诠释了朴素的修道院艺术。在抄本的制作中, 逐渐发展出了细密画师、古文师、抄经师、润色师等细分工种, 涵盖了装帧、金饰、搪瓷、编织、铸造等一系列工艺。 修士们在图书馆、抄书馆和手工作坊、园田土地之间来回穿梭, 以其勤奋与对财富的审慎态度, 创造出一种返璞归真而又教养极深的艺术风格。9 世纪出现的《乌得勒支诗篇》(Utrechter Psalter, 图2) 开创了不同于传统泥金彩绘手抄本的另一种描绘风格: 轻灵、活泼、动感,而富于叙事趣味的线描风格。虽然同属于加洛林艺术的产物, 但它更趋近于僧侣文化所钟爱的质朴凝练、言简意赅。尤其那种单色勾勒、近乎即兴的描绘手法, 与宫廷造物中庄重而近乎冷峻的皇家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它开创了另一种艺术造像的传统, 即艺术为更朴素的大众服务。
从亚历山大大帝引领的古典盛期, 到君士坦丁大帝去世的漫长阶段中, 艺术始终致力于描摹一种人格化的多重信仰。形形色色的典型的奥林匹斯神祇以完美的肉体形态展现出造型艺术所能达到的“美” 的程度, 也即对自然的理想改造。无论青春强健的阿波罗、孔武有力的赫拉克勒斯, 还是妩媚多情的阿芙洛狄忒, 都以无与伦比的完美性与典型性刻画出一种不容置喙的美感标准。而跻身其中的《拉奥孔群雕》在造型上属于极为矛盾的异类: 一位虚弱、失败的英雄, 身边伴随被惩罚与献祭的幼子。雕塑刻画的是与“完美” 相对的“不完美”, 是人生的痛苦,以及希望的毁灭。无怪乎李格尔在《拉奥孔群雕》上几乎看到了“基督教艺术的先驱”。这种对北方艺术风格的敏锐感知不无道理。随着条顿骑士团不断占据东北欧的广大地域, 这些地区也被全面地基督教化。自13 世纪起, “忧患之子” (vir dolorum) 与“圣母怜子” (Pietà) 一类的图像便在欧洲北方地区广泛流行(图3)。14 世纪与15 世纪的北方哥特式艺术中, 虔修图像受到中世纪晚期方济各会与德国神秘主义等思潮的影响, 尤其钟情于展示悲伤、沉郁的题材。术语“虔修图像” (An-dachtsbild) 特指一类能够助力于信徒观者之祈祷或沉思的基督教图像。其传统题材尤其强调刻画基督及其身边人物的苦难与悲痛。它由德国西南部的修道院文化孕育而出, 不仅出现在教堂内的祭坛屏上, 也以雕刻、版画等小型形式进入家庭供奉环境中。其内容从耶稣受辱与服刑的累累伤痕之苦楚, 到奉献亲子的玛利亚怀抱圣体之哀恸, 到施洗者约翰的断头之悲怆, 到圣维罗妮卡的丝巾上沾染的血汗之凄婉; 更有甚者, 直接展示十字架、长矛、鞭、荆棘冠、醋、盛血的圣杯等“受难之器” (Arma Christi) 的图像, 极尽渲染神之子牺牲之烈度, 激发观者的宗教激情。此类图像的流行, 无疑显示出当时宗教文化与大众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