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逊的《克拉丽莎》 与18世纪英国的性别与婚姻
编者按
本文将《克拉丽莎》置于18世纪中期英国情感史这一背景中进行考察,以此说明两点:其一、克拉丽莎的人物形象与18至19世纪性别差异观念的形成紧密相关;其二、她对纨绔子弟勒夫莱斯的拒绝呼应了17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的现代婚姻契约观,两人之间的周旋映照了18世纪对于单身女性和女性友谊态度的转变。《克拉丽莎》深入回应了乡绅阶层与早期资产阶级关于性别、婚姻与友情的话语,证明小说的崛起与现代情感的诞生相互依存与渗透。
作者简介
金雯,女,美国西北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8世纪英国文学、20世纪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塞缪尔·理查逊
18世纪中期,刚诞生不久的现代英语小说尚未形成固定的形式规范,时而略显笨拙,时而夸张随意。与此同时,早期资产阶级与乡绅阶层的情感结构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动,他们开始尊崇“情感个人主义”,对个体独立的向往、同情、真诚等现代情感因此逐渐形成,但强制规范情感的保守力量也以各种面目存留下来。性别观点及男女情感模式在不同潮流的裹挟下艰难又无可否认地发生着转变,纠结着许多无法解开的矛盾。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是“情感时代”与小说崛起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对18世纪情感结构与早期英语小说研究都极为重要。他于1747-1748年首次出版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位于小说史与情感史的一个交点,与英国18世纪中期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不可割裂,不仅折射了18世纪新崛起的情感结构,也通过形式和主题等不同路径对之进行干预,对修正与充实关于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的认识至为重要。在这个大背景下考察该小说,我们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克拉丽莎的人物特征和情感轨迹与18世纪关于性别身份与私人情感——尤其是婚姻与友情——的话语有何关联?该书信体小说所采用的叙事形式与男女情感模式的变迁之间有何互动?考察这些问题有利于我们初步了解早期英国小说与情感史研究的关系以及文学介入情感史研究的基本路径。
情感史聚焦于文学、文化与情感结构变迁的关系,吸纳了福柯开创的“身体政治”和伯明翰学派“情感结构”等研究范式的基本思路,深化了对主体与意识演变历史的研究。[1] 这个领域近十多年来发展迅速,研究范畴包括“affect”(可译为“感受”、“感情”或“感触”,指主体尚未意识到的强烈生理感应)概念,也涵盖了日常情绪,使用“emotions”或者“feelings”这样比较中性的词指涉经过主体阐释、定性的情感。[2] 情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综合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发端很早,理论渊源众多,2000年左右成为显学,目前仍然蓬勃发展,并处于回顾自身历史、进行学科整合的关键时期。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情感史的建构中居功至伟,而情感史又反过来丰富了文学、文化研究中自威廉斯、福柯、德勒兹以来建立的探讨情感形成及演变历史的传统。以这些广义的“情感”为关键词(包括emotions、feeling、affect等),学者将叙事形式及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变迁与“内心”观念的转变相关联,在文化批评中融入对话语体系所依赖的意识与生理基础的分析。威廉·莱迪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在《情感导航》一书中业已证明情感结构对政治与社会史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大革命前的法国小说、戏剧和绘画等体裁构建了崇尚真诚与坦荡的“感性文化”,成为革命发生的基石。[3] 英语小说脱胎于早期现代罗曼司和“生活写作”(life writing,包括自传、日记和书信等),自17世纪末诞生之初就以同时代生活为背景阐释私人情感与欲望。正是在提升自身文学地位、开拓读者群的过程中,18世纪小说将世俗情爱变成认知、哲学和社会问题,在职业阶层和乡绅阶层的日常生活细节中挖掘道德和文化批判的空间,因此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代情感史研究的一个焦点。
《克拉丽莎》以书信体小说形式让人物不断地进行“即时写作”(write to the moment)[4],把未经疏通和消化的情绪全盘呈现在纸面上,对18世纪内心和情感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本小说的第三版于1751年发行后,理查逊又将小说中有关情感与道德的感悟抽出来,按字母顺序排列,结集成册。[5] 但这个集子并不能概括理查逊的小说,我们必须将它放在流动的情感集合中进行阐释,正如当代18世纪小说研究者丽萨·曾施恩所言,她在讲授《克拉丽莎》的时候,不愿意“落下小说的任何一个字”。[6] 这本小说在情感史上的重要地位恰恰是因为它揭示了情感的动态本质和复杂层次,这也正是读者和研究者在这座巨型数据堆前流连忘返的缘故。
《克拉丽莎》虽然是篇幅最长的英语小说,但其情节并不复杂:富有的乡绅人家的小姐克拉丽莎被同阶层纨绔子弟勒夫莱斯追求,但其家族逼迫她与一年长富商成婚,勒夫莱斯顺势诱拐,带她出走,继而骗她至伦敦。此时,克拉丽莎断定勒夫莱斯有重大人品缺陷,拒绝接受他的求婚,但却不幸被其奸污,不堪精神压力,最终抱病而终。小说的叙事主要由两组信件构成,即女主人公克拉丽莎与女性友人安娜小姐的通信以及男主人公勒夫莱斯与男性友人贝尔福德之间的通信,不同人物经常会对同样的事件做出不同的阐释,也时而分担对不同事件的叙述,这些书信详细记录或概括了特定事件发生时写信人的心情,很少掺杂事后的反思和矫正。小说利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描写了男女在婚姻选择中的不同情感模式,不仅表现并召唤男女交往的新模式,同时也铸就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艺术,这种新型情感模式的形成与叙事形式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议题。本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第一、提出并辨析“情感小说”这个体裁,说明其形式特征与18世纪英国文化的关联;第二、讨论克拉丽莎人物形象刻画与同时期关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特点话语之间的关联;第三、分析伴侣式婚姻和单身女性形象在18世纪的发展及其在小说中的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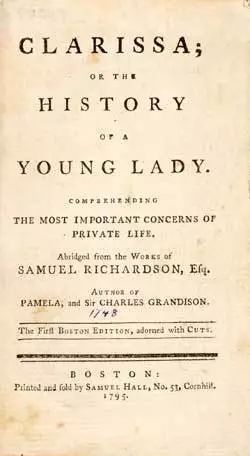
1795年版《克拉丽莎》标题页
“感伤小说”和“情感小说”之辨
《克拉丽莎》诞生的年代是医学和哲学话语对情感的发生机制和道德与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的年代,因此这部小说经常被纳入“sentimental novel”这个叙事体裁的范畴,中文一般将该叙事体裁译为“感伤小说”或“伤感小说”。“sentimental novel”这个术语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得到了普遍运用,但若追溯其根源,一般可推至18世纪四十年代,尤其以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Pamela,1740)、《克拉丽莎》和《查尔斯·格兰迪逊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1753-1754)为早期代表。[7] 该术语及其中文对应术语“感伤小说”都包含以情动人的意味,这个体裁通常描绘了“一种失衡的心理状态——沉溺于以悲伤和悲悯为主的情感,根据情绪反应来决定对于道德问题的立场”[8]。理查逊的小说部分符合关于“sentimental novel”的一般定义:的确,理查逊经由医生乔治·谢尼(George Cheyne)的介绍受到洛克心理学的影响,在小说中经常呈现外界刺激对人物情感的强烈影响,他的女主人公往往受尽屈辱胁迫,引人同情。克拉丽莎心力交瘁而亡这个结局,就引得小说内外的旁观者泪湿前襟,也印证了同时期以及后世学者对于此类小说的惯常理解。
但理查逊的小说也有诸多与这些理解相抵牾之处,并不全然致力于引发读者的认同,使之涕泪交加。他的小说不仅局限于探讨强烈情感发生的机制,更在意如何通过常年的习惯来调节情感和进行自我管理。[9] 在刻画克拉丽莎时,理查逊非常注意描写情感的克制和细腻:克拉丽莎一度为自己强大的自制力而欣慰,即使在她濒临死亡、周围人都为她扼腕唏嘘的时候,她也没有失控,而是给自己设计好棺木,安然准备前往天国。瓦特早就指出,描写克拉丽莎死亡的段落类似于17世纪流行的葬礼文学,葬礼文学往往意在揭示死亡之后能获得正义这一道理,与理查逊在《克拉丽莎》中流露出来的超越物质世界的信仰是一致的。[10] 也有学者指出,理查逊并不希望人们对克拉丽莎之死产生巨大的同情,因为同情并不能使人在道德上得到修正,故而借用小说中贝尔福德这个人物形象说明,人们对克拉丽莎的仿效应该是一种类似皈依基督教的理性选择。[11]可见,理查逊对于情感的态度明显有别于卢梭所代表的典型的感伤主义,他并不相信天然的情感具有道德属性、只要被唤醒就能引人向善。
因此,为了比较公正地阐释情感在小说《克拉丽莎》中的地位,我们恐怕需要一个更为宽泛、更具弹性的概念。不少外国学者选择以“novel of sensibility”或“novel of sentiment”这两种表达方式来替代“sentimental novel”,借以谈论包括18世纪小说在内的以情感为主题的小说,而不局限于赞同或鼓励强烈情感的小说。[12] “sentiment”和“sensibility”都是18世纪开始被频繁使用的词,根据《牛津英语大词典》给出的相关释义,“sentiment”表示有一定精神层面、与理想事物相关的情感,在17至18世纪之间,与“情爱”关系密切;而“sensibility”在18世纪初期就开始表示情感敏锐这种特性,尤其指温和细腻、以理解体恤他人为核心的情感倾向。这两个词都有褒扬意味,都比较符合小说关于克拉丽莎纯净道德观的描写,且不像“sentimental”那样限定了整部小说的价值取向。与此相应,中文也应该有一个更宽泛准确的描述方法,以指称18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以情感为中心的小说,笔者认为可以借鉴“novel of sensibility”或“novel of sentiment”这两种说法,称这类小说为“情感小说”或“写情小说”[13]。
笔者提倡“写情小说”这种称呼也与弗莱的文章《情感时代刍议》有关。弗莱认为,18世纪中期和晚期的诗歌和小说流露出将文学视为“过程”的理念,书信体写作和诗歌中的不规则格律无不在印证与凸显这一点,这些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弗莱称之为“情绪”的无法消化或割舍的情感,既不能被虚构的人物驱除,又让读者欲罢不能,他据此提出了“情感时代”(age of sensibility)这个概念,以描绘此类文学占主流地位的时代。[14] 弗莱的这个术语为我们描绘理查逊小说提供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克拉丽莎》这部书信体小说强调“即时写作”,让人物袒露其情绪纷乱、无法平息的状态,与弗莱对情感的理解有相通之处,称之为“novel of sensibility”即“情感小说”应该比较妥当。将《克拉丽莎》称为“情感小说”,表明它不仅刻画与激发了强大的情感反应,对情感模式及其变迁进行了剖析和审视,也忠实于展现情感所蕴含的矛盾和死结,用捕捉当下的文学语言暗示情感必然溢出主体控制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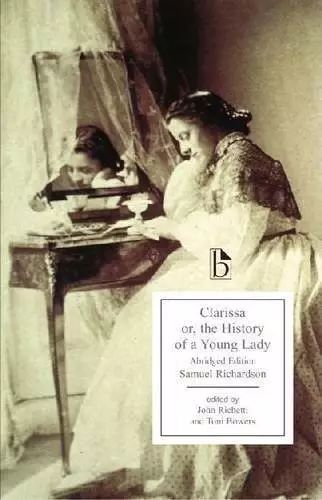
《克拉丽莎》
克拉丽莎形象的谱系
在《克拉丽莎》中,理查逊的女主人公性情贞洁,恪守礼数,似乎是一个没有激情的女性。她对浪荡子勒夫莱斯有些好感,但并不形之于色,只在极少数场合流露妒忌或怜惜之情,一次是对勒夫莱斯传说中曾经染指的农村女孩深表鄙夷(see Clarissa:285),一次是因为勒夫莱斯假装生病而大惊失色(see Clarissa:678-679)。即便如此,她对勒夫莱斯的好感也不够深刻,以至用嘲讽的口气来讨论他突变的态度,例如在谈到他有次下跪恳求时,克拉丽莎不无讽刺地说“他膝盖很软”,与他在冲突争执中的“傲慢”性情相悖(see Clarissa:166)。她也是最早揭示他的姓名预示不详的小说人物,认为他“缺一颗心”(Clarissa:184),暗指他名字的字面意义为“没有爱”(Love-less)。对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而言,克拉丽莎不易动情的特点也是一目了然的。勒夫莱斯把她诱骗至伦敦后,邀请贝尔福德等酒肉朋友到寓所聚会,贝尔福德之后在信中认为克拉丽莎的特点在于“全部是头脑”(Clarissa: 555),言外之意是没有常人的情感与生理需要,只受理性控制,追求精神的高贵。这个没有“身体”的女性形象在西方小说和文学中较为罕见。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偶然可见处女形象,如斯宾塞的仙后,这类人物的原型可以追溯至以“头脑”命名的罗马女神密涅瓦、向柏拉图传授精神之爱的古希腊女性狄奥提玛以及奥德赛贤淑的夫人佩内洛普等;但总体而言,古希腊神话中预言家特瑞西阿斯关于女性性欲更强的判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催生了海伦、阿弗洛狄忒、狄多等欲望强烈的女性形象,经由骑士传奇、爱情诗、喜剧等体裁延续至笛福、贝恩、海伍德等早期小说家的作品中。

《克拉丽莎》插图
那么,克拉丽莎这个形象是孤立现象还是某个话语谱系或知识类型中的一部分呢?她与同时代有关女性欲望的话语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不少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学者的研究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很具启发意义。达伯霍瓦拉指出18世纪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人们开始认为男性性欲更加强烈,而女性比较被动,贤淑的女性很可能并没有性爱欲望。这个变化是克拉丽莎形象出现的重要文化条件。这种转变与17世纪晚期兴起的浪荡子文化有关。尽管浪荡子唐璜、乔亚瓦尼等人物在欧洲民间传说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在英国形成的直接原因却是查理二世及其廷臣的淫乱作风渗透了整个上层阶级,许多下层女性遭受诱奸,被抛弃后流落风尘,有些乡绅和中产女性也不幸经受了相同的命运。浪荡子文化以女性幸福为牺牲品,引发了为女性申诉和辩护的声音,不少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英国戏剧和小说都以女性受害为主题。以贝恩(Aphra Behn)的戏剧《复仇》(The Revenge,1680) 和曼利(Delarivier Manley)的《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1709)等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讲述了女性受上层男性欺骗和引诱的故事,传播了女性欲望不如男性强烈、只是无端受害这一新观点。[15]
与此同时,世面流通的“女德训诫”(conduct books)这类书籍也明显增多,大多旨在劝诫女性恪守贞洁克己的美德,避免被诱奸的命运。1695年出版许可法令(Licensing Act)被废除后,女德书籍的数量一度上升,至18世纪中叶达到高峰,这类书籍作者多为牧师及中产阶层的年长男性,也有中上阶层女性,包括克拉拉·里弗(Clara Reeve)和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等女作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托马斯·马里奥特所作《女性礼仪》(1759),该书序言表示,时下女性教育几近荒疏,危害甚巨,而古罗马时代最为尊崇的美德——“贞洁、对待婚姻的忠诚”[16]——的沦丧正是造成共和国晚期内战的原因,由此可见女性美德培育的重要性。马里奥特同时指出,女性不仅有责任提高德性,也很适合这项任务,因为她们比男性“更为柔软,天性更为驯顺,易于教化,更能够接受并保持印象”。[17]马里奥特的这些话印证了达伯霍瓦拉的观点,说明在18世纪中叶女性贞洁是被反复强调的女性美德,而女性也被认为具有保持这种美德的天性,只需加以教育即可。同时期同样流传广泛的《致年轻女士的布道词》说得更为明晰:女性的美德非常重要,“塑造男性的举止有很多方法,没有哪种可以与女性的谈话媲美”,前提是女子拥有“美德与理解心”。[18] 可以说,克拉丽莎的出现标志和开启了倚重女德的文化潮流,贞洁等美德被视为女性天然的心性,也成了她们必须背负的重担。
正是贞洁和自律赋予了女性一定的文化权威,才使她们成为现代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核心。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欧洲,“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实现了分离,随着绝对君权与绝对父权的衰落,市场与家庭生活的文化地位日渐增长,成为私人领域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和同时期的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小说也开始以私人领域为主要背景,干预政治议题,塑造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的崛起催生了麦基恩所提出的“家居生活成为艺术形式”(domestication as form)[19],也同时促进了“女性权威”[20]。当然,所谓的女性权威是一柄双刃剑,取决于女性是否将自己局限于温驯贞洁这些美德,这种限制到了19世纪中叶愈加明显。美国历史学者托马斯·拉奎尔在经典之作《创造性别》一书中指出,从18世纪开始,英语世界的人们开始普遍认为女性与男性在生理构造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性别,生理性别的观念因此形成,随后逐渐得到巩固与强化,到了1840年代,“被动”和“没有激情”已然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一种普遍的成见和期望。[21] 究其根由,不仅是因为有医学的支撑,也与18世纪以来私人领域的崛起紧密相关。[22]

《勒夫莱斯强暴克拉丽莎》,爱德华·路易斯·杜巴弗,1867
《克拉丽莎》中女主人公流露出来的情感观念与上面所勾勒的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历史转折存在明显的共振。她在很多段落里都认为女性不能在寻求感情和婚姻的过程中主动出击。与勒夫莱斯私奔后,密友安娜劝克拉丽莎想办法让勒夫莱斯尽快与她成婚,以便保持名节,克拉丽莎发出了以下惊叹:“什么,让我去激将一个男人来娶我?叫我想办法加速他迟缓的决定吗?我已经丧失了一次发自内心、为了我自己而想要成婚的机会……现在却要让我去威胁他与我成婚!这怎么可能,亲爱的!即使这是件正当的事,符合谦逊与自我(或者说骄傲)的需要,还是会多么的困难!”(Clarissa:589-590)这段文字开头就用了“激将”(challenge)一词,表明克拉丽莎将男女之间的求爱比作角力,认为女性不能是进攻的一方,她在欲望上的被动符合18世纪中期文学和戏剧的一个基调,即减弱女性欲望,将诱奸女性行为的罪责放在男性身上,批判王政复辟之后形成的浪子文化,同时教导女性恪守贞操。这个时期,作为弱者、被动方和性欲受害者的女性形象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最终在理查逊的人物刻画中得到了空前的道德化处理。被动在克拉丽莎身上显现为矜持自重的美德,而作者也通过不断暴露勒夫莱斯的各种缺陷对女主人公的审慎表示支持。不过,与达伯霍瓦拉和拉奎尔所强调的“被动”形象不同,克拉丽莎还有明显的自主诉求,延续了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初期戏剧中女性形象的另外一面。已有学者指出,对于浪荡子传统的颠覆和反思在此时的戏剧中不仅催生了对受害女性的刻画,也催生了性欲旺盛的女性角色以及男女易装与启用女性演员等现象,使得王政复辟时代的部分戏剧成为对女性权益和本性的认识发生变化的表征与动因。[23]《克拉丽莎》虽然塑造了一个“清心寡欲”的女性,却与包含早期女性主义色彩的戏剧和小说暗通款曲,直接发出了女性婚姻自主的宣言。
克拉丽莎深知,在婚姻这场男女对峙的战役中,如果自己采取“主动”,将正中对方下怀,无法遵循“发自内心,为了我自己”这个前提。也就是说,如果她催促勒夫莱斯和她结婚,不仅将违反女性的矜持原则,更与自己的意志相违背。[24] 克拉丽莎的每一段文字都和这段一样迂回曲折,绝不是在机械地宣扬女德。这也就是为什么瓦特要为理查逊开脱的原因,瓦特认为他虽然有道德训诫师的一面,但作为作家的一面更为突出,克拉丽莎的自我保护符合新教和早期资本主义所催生的个人主义,也预示了康德所代表的道德抉择上的内省传统。[25] 克拉丽莎的矜持克制和对个人权利的捍卫将她与传统意义上的受害者区别开来,她并没有因为冲动而爱上勒夫莱斯或者因为意志软弱而失身。勒夫莱斯出于无奈只能采取强暴的手段来征服克拉丽莎,只是此举南辕北辙,彻底葬送了他与克拉丽莎修好的可能。克拉丽莎的悲剧不只是简单地因为受到了浪荡子的诱拐,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十分复杂。
僭越女德
克拉丽莎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她与尊崇父权和夫权的女性美德观有诸多抵触。她的美德不仅表现为对激情的控制——“我们女性的激情,抑制起来不太痛苦”(Clarissa:550)——也体现了诸多现代特征。在贴身保姆兼家庭教师诺顿小姐的教育下,她不仅谈吐得体、文笔娴熟,同时也有出人意料的顽强和坚韧。她虽然把祖父遗嘱中留给自己的地产让渡给父亲,并声明不愿意与之对簿公堂,也在出走后因为父亲对她的毒咒而痛苦万分,但她对父亲的决定却并非言听计从。在家人逼迫她嫁给暴发户索尔姆斯先生的时候,她背着他们继续与勒夫莱斯通信,并对父权表示不满,勒夫莱斯正是利用了她对家长权威的反叛,才成功诱使她离家。受到勒夫莱斯的诱骗与强暴之后,克拉丽莎又想尽办法逃离他的控制,她的两次逃离是理查逊第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帕梅拉所没能做到的,也是她的强烈自主意识在小说空间规划上的表现。
在读了《克拉丽莎》分期出版的第一部分(第一至第三册)后,曾经嘲弄过理查逊《帕梅拉》的菲尔丁对自己的对手表示了欣赏,也充分领会到理查逊笔下人物的复杂程度,并评价道:“克拉丽莎太恭顺了,又太不恭顺了。”[26] 在涉及婚姻和感情的问题上,克拉丽莎非常坚定地要求选择权,她所坚持的“发自内心,为了我自己”而结婚的观点也呼应了洛克的婚姻契约论[27],体现了作者对于女性在婚姻中是否拥有选择和自主权的探讨。对于理查逊来说,女性在婚姻中应该拥有自主权,其最深层的涵义是有自主判断对方的人品和道德水准的权利。“道德品行”(character)这一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词,是理查逊的《帕梅拉》和《克拉丽莎》中的女主角们需要独立做出判断的最重要事项,是她们愿意达成婚约的基本条件。这个词在理查逊编撰的《日常书信集》(1741)中也有很突出的地位,该书信集按照家庭事务各名目分类,有一部分专论男子如何请求心仪女子父亲的首肯以及女子如何与自己的父亲沟通,在这些信件里,男方的道德品行是反复提起的首要标准。[28] 对男子品行的注重并不难理解,18世纪女性道德权威的形成和对浪荡子的批判风潮都对男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克拉丽莎在自己的信中始终强调男子的品行和精神境界,在写给安娜小姐的一封信里,她解释了为什么勒夫莱斯一开始对她有一定吸引力,借此罗列了自己对男性的一般原则和具体要求。这一串要求现在看来也会让许多人汗颜:

如果说勒夫莱斯在我看来还勉强可以,那是因为没有对比。假如他们给我一个能与之较量的男人——冷静理智、美德、慷慨无私、自食其力,对他人的悲惨遭遇慈悲以待,对有恩之人涌泉相报——假如勒夫莱斯有这样一个对手……他们就不用指责我顽固不化了。那个男人的身材样貌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我们女人做出抉择的标准应该是心灵,只有心灵能保证男方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表现良好。(Clarissa:181)

随后,克拉丽莎又借用婚姻契约论的语言,说明自己择偶要求高的原因。她认为女性在婚姻中多为“服从”的一方,相应的,这也就要求男方有值得服从的地方:“服从一个自己选择的男人比起听从一个避之不及的男人要轻松愉快得多吧,自己选的,即使脾气大也不要紧。”(Clarissa: 182)克拉丽莎并不质疑大多数男性在婚姻中占据主导的现状,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所说共同利益与财产的事务“自然落在男方身上,因为他们更能干强壮”[29]的说法相差无几,但她同时又对这种服从提出了很难企及的条件。克拉丽莎给包括菲尔丁在内的读者的印象是一个温顺又逆反的矛盾体,但无论如何,克拉丽莎对婚姻的要求有明显超越之前小说、戏剧和诗歌的元素。

《帕梅拉》插图
克拉丽莎的逆反侧面也可以在下面这个经典段落中得以管窥:“真正的慷慨依托于伟大的灵魂。它激励我们为同类做出超越义务的让步,催促我们向需要解救的人们伸出援手,不必等他们开口。先生,慷慨的精神不会允许另一个高贵的头脑怀疑它高贵而美好的愿望,更不会放纵自己去冒犯、突袭别人;假如这个人因为逆境、厄运或偶然因素被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中,就更不可能了。”(Clarissa: 594-595)这一段引文出现在克拉丽莎和勒夫莱斯到达伦敦之后。当勒夫莱斯试图偷窥她的信件、限制她的行动、多次粗暴要求她的陪伴之后,她在这段引文中给勒夫莱斯上了一堂道德课,解释什么是真正的慷慨。和上一段引文一样,这段引文说明克拉丽莎理想中的男性具有和她一样高尚的精神境界,这一思想的叛逆性质在于它很快就会延伸而成为一段对男女关系的革命性理解。这个逻辑跳跃果然发生了,这一段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小说中最美妙的一句话:“婚姻是友谊的最高形式:美满的婚姻给我们甘苦与共的伴侣,将忧愁减半,让幸福加倍。”(Clarissa: 595)这句话对婚姻的解释是前所未见的,婚姻双方的关系被定义为友谊,成为普遍的善举和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延伸,需要以高尚灵魂之间的共鸣为基础。如果说之前克拉丽莎对男性品德的要求还囿于契约论的平等交换逻辑,到了这里她已经完全抛却了契约论,提出了对婚姻的全新理解。
克拉丽莎对理想异性爱情的勾勒,让我们联想到劳伦斯·斯通率先提出的“伴侣式婚姻”在18世纪崛起这一论题。斯通指出,18世纪出现的“情感个人主义”削弱了利益婚姻的比例,提升了情感在婚姻中的地位。[30] 在上述那封信的逻辑转折里,克拉丽莎用自己的方式勾勒了“情感个人主义”发生的途径,她的话语表明,当婚姻契约不再具有永久的效力时,婚姻就需要更为强有力的纽带,而男性的品行——或者说男女品行的对等——在女性心目中跃升为最牢靠的婚姻纽带之一,与金钱和利益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而这反过来又将婚姻关系与契约论分离开来,迂回地实现了一种革新。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克拉丽莎对婚姻的理解其实也并不是那么新颖,至少可以部分追溯至她的新教背景。斯通指出,新教改革以“神圣婚姻”取代了天主教的禁欲思想,英国国教神学家将已婚状态奉为基督教徒的理想标准,强调感情联系是婚姻的必需品。[31] 1642年,清教徒牧师丹尼尔·罗杰斯就在自己的婚姻守则中指出,夫妻关系最为根本,故而上帝会让夫妇拥有胜过朋友的“隐秘的心灵共情”(secret sympathy of hearts)。[32] 从某个角度看,克拉丽莎的婚姻思想是她宗教虔诚的自然延展,这在小说的出版后记中可以得到证实,其中清楚记录了理查逊对自己小说宗教作用的关心。[33]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进步”与否这一概念来描述克拉丽莎对婚姻与女性的思想,只能说新旧思潮汇集在她身上,催生了一场变革,但变革所遮蔽的思想矛盾最终还是会显露出来。
当然,这部让浪荡子袒露心声的小说同时也说明神圣的爱情难以获得。因为勒夫莱斯始终没有达到克拉丽莎所想象的道德高度,克拉丽莎便一直没有真正地爱上他。既然找不到类似友谊的爱情,那么克拉丽莎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她自己的话,即纯粹的友谊相当于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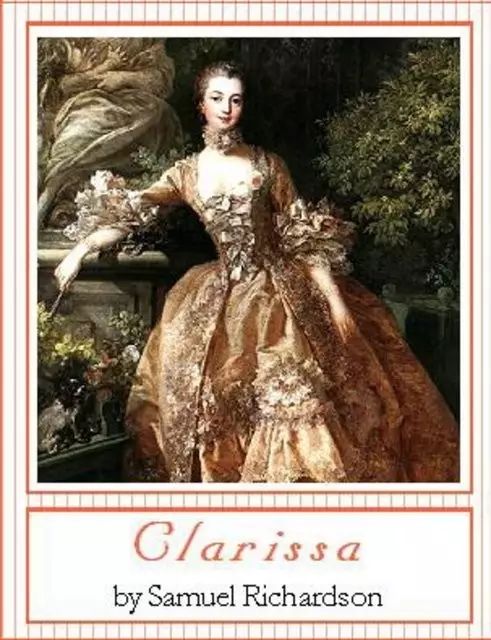
克拉丽莎肖像
克拉丽莎唯一感受到的纯粹友谊来自安娜小姐,在她受勒夫莱斯诱骗离家出逃陷入困境时,安娜不仅坚持提供金钱支援,还提出和她一起去伦敦,虽然这一提议没有被克拉丽莎采纳。正因为如此,她与安娜小姐的关系在小说里成了克拉丽莎唯一认可的亲密关系,被赋予了崇高的类似婚姻的涵义。她多次称安娜小姐为“爱人”(lover),并把自己的戒指作为遗产赠送给这位唯一的朋友。与此同时,克拉丽莎对传统婚姻的兴趣也丧失殆尽,并在多封信中明确表达了对单身生活的向往(see Clarissa:507, 514, 593)。她的选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18世纪早期的女性思潮相吻合。
对单身女性以及女性间友谊的刻画是早期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主题,克拉丽莎的情感选择与时代话语进行着密切对话,但鲜有人评论。18世纪不仅是伴侣式婚姻崛起的时代,也是单身女性形象——忠贞无欲的女性和受浪荡子迫害的女子——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范畴的时代。在17、18世纪英国,女性和男性的单身状况相当普遍,年满50岁而从未结婚的女性比例在1675年到1799年间“达到将近25%”[34]。在这个时期,战乱、缺乏嫁妆、家庭重担等理由都可能导致女性单身,在有些城市里,单身女性的人数可以达到成年女性的三分之一强。[35] 更重要的是,“单身女子”在18世纪成为一种显性社会身份,进而作为一个问题而进入了文化讨论。基于对人口数据、社会话语以及女性写作的研究,弗洛德指出,16世纪及之前很少有单身女性这一文化形象,只有少女(maiden)形象。17世纪上半期出现了表示长期未婚女性的字眼,如spinster和singlewoman(这个字原本具有妓女之义),但意义中性,尚无附加评判与感情色彩。由于战乱和女性意识提高等原因,17世纪单身女性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范畴,沾染上了负面色彩,女性不婚不育被认为是一种名为“青涩病”(greensickness)的隐疾。[36] 到了17世纪末期与18世纪早期,围绕单身女性的社会争论更为激烈,出现了如匿名出版的《处女的辩白:又名论单身生活的十五处便利》(1707)[37]这样的不婚辩护书,而与此同时,单身女性又被视为亟须解决的问题和社会话语嘲讽的对象。换言之,在女性单身合理的论点日益高扬的同时,不婚女性又受到抨击,沦为被否定的刻板印象和深刻文化焦虑的外化标志。笛福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焦虑,他在1697年提议建立一所女子学院,以训练年轻女子顺利步入婚姻;到了18世纪二十年代,他又在杂志上写了一系列讽刺奚落“老处女”的文章,开首一篇就名为《讽苛刻老处女》(1723)。[38]
18世纪强调夫妻间要形同密友,但并没有为找不到伴侣式婚姻的单身女性开辟社会空间,她们标志着乡绅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情感伦理的边界。这种排斥机制在18世纪小说史中也有所表现:单身女性一般作为有问题的次要角色出现,比如菲尔丁《汤姆·琼斯》(1749)中的维斯顿小姐、斯摩莱特《汉弗莱·科林科》(1771)中的塔比莎·布兰波、理查逊《帕梅拉》中的女佣朱克斯等。理查逊在《克拉丽莎》这本小说中对单身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但也并未跃出乡绅阶层和资产阶级情感伦理的界限,最终没有把单身这条道路变成社会所允许的现实。小说在这个问题上的摇摆也被两位主要女性角色所内化。虽然克拉丽莎不断提到自己如何向往单身生活,唤安娜为“爱人”,但她又不断劝安娜认真考虑接受追求者希克曼先生的爱慕之情,安娜也不断劝说克拉丽莎催促勒夫莱斯与她成婚。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她们之间的友谊表达的是女性对婚姻自主的坚持,她们的纯粹友谊为异性婚姻提供了一种模型,但当这种友谊抵触婚姻的时候,便充满了悲剧的可能。
将友谊置于婚姻之上的女性所遇到的社会阻力也通过小说的次要人物体现出来。克拉丽莎所尊重的表兄莫登就对女性间的友谊表示蔑视,他说:“友谊是炽烈的火焰,女性的头脑很难驾驭;只有很少的女性能够让友谊之火长燃,大多数人会因为胆小而逃跑,或变得举止荒诞……婚姻是友谊的最高形式,一般会吸纳哪怕是最浓烈的女性友谊。”(Clarissa: 1449)他重复了克拉丽莎说的“婚姻是友谊的最高形式”这句话,但彻底篡改了它的含义,使之变成从友谊到达婚姻的单向路径。莫登的质疑是西方思想传统在小说中的镜像,映照了蒙田曾说过的类似的话。在《论友谊》一文中,蒙田认为“以女人寻常的能力来说,她们难以胜任维系这个神圣纽带所需要的交流和沟通;她们的灵魂不够坚强,不能承受如此沉重而持久的关系”[39]。小说中,安娜小姐首先注意到莫登的狭隘,她在给克拉丽莎的一封信中就直接说莫登与其他男性人物是一丘之貉,不配“先指责别人”(Clarissa:1314)。对安娜的犀利和战斗性,作者则给予了暗暗的赞许(至少是许可),借她之口对莫登加以嘲弄。不过,话说回来,理查逊并没有让安娜成为打破乡绅阶层婚姻观的女勇士,对她也加以了制约:虽然安娜一开始瞒着母亲与克拉丽莎通信,最后还是与母亲开诚布公;一开始嘲笑希克曼笨拙,最后还是满足地踏入了与他的婚姻。理查逊并不想完全颠覆女性的传统地位,克拉丽莎和安娜小姐的反抗都没有当时已经出现的注重才学的“蓝袜子”女性的影子[40],她们所体现的是乡绅及资产阶级情感伦理的内在矛盾。
因此,女性间的友谊是《克拉丽莎》开拓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学母题,体现了这种情感对于异性婚姻的重要补充作用,也显示出其脆弱和艰难。同时期出现的相关文学案例包括玛丽·马斯特斯的《日常书信与应景诗歌集》(1755),其中不少诗歌描写了作者对女性密友的情感,以及萨拉·司各特的以女性乌托邦为题材的小说《千禧年殿》(1762)。[41] 在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2)中,女主人公于丽也有一个表姐妹克莱尔,两人是互相倾诉秘密的知心密友,而克莱尔也对倾心于她的绅士说自己最关切的是与于丽的友情,并告诉求婚者:“作为一个女人,我是一个魔鬼,脾性古怪,不知为何喜好友谊多于爱情。”[42] 不过,在18世纪的欧洲文学中这样的例子毕竟不多,直到19世纪女性友谊才在小说中成为一个固定母题。根据莎伦·马科斯的论述,女性自主和女性间友谊与传统异性婚姻的矛盾在19世纪中期的小说里得到和解,女性友谊成为异性婚姻的情感演练场和女子之间的互助机制,与异性婚姻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43] 但这种和解在婚姻观念和女性地位都处于动荡中的18世纪小说和社会中还是很难想象的,克拉丽莎的死亡与单身女性的尴尬境地有着互为映照的关联。

卢梭《新爱洛绮丝》插图
在理查逊笔下,单身女性形象和女性友谊的被污名化凸显了出来,充分昭示了18世纪作为新旧交替时期所催生的社会和情感结构内部的矛盾。克拉丽莎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体现出了这些矛盾的激化,受骗失身的她没有清晰的生路,只能走向死亡。小说并没有对自身所揭示的问题表达明确的立场,只是用不同人物的互相评判暗示各种话语力量的角逐。借用福柯在《性史》中对性爱话语史的论述,我们可以说18世纪中期是情感成为显性分析对象的时期,但关注情感并非等同于情感的解放与自由,有关私人情感的各种相互冲突的话语必然与新的身份与阶层(如单身的上层、中产女性)的形成纠缠在一起,成为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手段。
结语
18世纪是性别差异观念形成和伴侣式婚姻崛起的世纪,也是单身女性成为刻板印象的世纪,各种互不协调的声音互相干扰。婚姻契约的修正只是保证了女性在婚姻选择和家庭管理方面的权利,关于女性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却并无定论,不同的话语和思潮因此交叉碰撞。小说不仅表现了这些纷争,也参与其中。《克拉丽莎》对日常生活状态下的情感逻辑的表现达到了几近完美的地步,巧妙地将各种社会话语糅合在一起,包括作者略显保守的姿态、浪荡子对女性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女性争夺社会权力(包括写作等公共活动)的早期女性主义声音。这些话语互相博弈与渗透,没有哪种占据了明显的主导。理查逊以历史上最长的英语小说来描绘绵延不绝的情感角力,重在过程,而非结局。它不只是引发了读者的唏嘘,也不只是触动了他们见贤思齐的愧疚感,更重要的是深入细致地剖析了18世纪英国乡绅阶层的情感结构及其死结。
当然,小说的伟大并不能掩盖作者的局限,理查逊作为道德说教家的一面不容置疑。在与不同女性朋友的通信中,他都发表了自己关于《克拉丽莎》的阐释,试图影响他众多女性读者的阐释立场。他斥责勒夫莱斯的强烈控制欲,又同时教导她们不要认同安娜小姐对母亲的反叛和对追求者希克曼的戏弄。这种说教意愿在他书信的其他内容中也有充分体现。在一封写于1749年12月5日的给女性朋友弗朗西斯·格莱恩尔的信中,理查逊专门提及了对“激情”(passion)一词的理解,强调说它看上去包含了被动受苦的意味,实际上却具有“主动”的性质,所以任由情感张扬会带来苦难,但主动控制和塑造情感就可以维持心灵的平静。[44] 由此可见,理查逊经常扮演父亲角色,宣扬自己关于家庭和男女关系的看法,对女性情感提出规范:虽然他申明自己注重女性教育,却明确把这种教育局限于家庭管理,强烈感叹女性出没于公共场所的堕落。[45]
理查逊对新女性的社会前景并没有变革性认识,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特意塑造了查尔斯·格兰迪逊爵士这样温和多情的男子,却没有触及新女性的正面塑造。这个任务最终落在了女性作家的身上。伯尼的书信体小说《伊芙琳娜》(1778)可以说是对《克拉丽莎》的续写,小说在开头简短重复了一个类似克拉丽莎的悲剧之后,便开始描写女性走出家门、频繁暴露于公共场所后发生的状况,表现出理查逊所不愿表达的对于扩大女性生活空间的乐观,也为之后简·奥斯丁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但是,《克拉丽莎》并没有被后起之秀所取代,它对早期现代私人情感的描写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之后的作品再也无法超越,它仍然是今天研究英国18世纪情感史所无法绕过的关键地标。
[1] See Michel Foucault,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Paris: Seuil, 1997, pp. 244-280;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28-135.
[2] 情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综合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成果,发端很早,理论渊源众多,2000年左右成为显学,目前仍然蓬勃发展,并处于回顾自身历史、进行学科整合的关键时期。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情感史的建构中居功至伟,而情感史又反过来丰富了文学、文化研究中自威廉斯、福柯、德勒兹以来建立的探讨情感形成及演变历史的传统。
[3] See Willia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41-210. 莱迪的主要论点是:路易十四治下,等级制度森严,情感庇护所应运而生,文学、戏剧等文化形式与哲学思想都歌颂良性情感的普遍性,突出真情实感在私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表现出对人性的乐观。
[4] Samuel Richardson,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ed. Angus Ross , New York :Penguin ,1985 , p .721.该版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747-1748年分三次出版的小说第一版,以下引用的《克拉丽莎》片段均出自该版本。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 See Samuel Richardson, Collection of the Moral and Instructive Sentiments, Maxims, Cautions, and Reflexions, Contained in the Histories of Pamela, Clarissa, and Sir Charles Grandison, London: printed for S. Richardson, 1755.
[6] Lisa Zunshine, “Teaching Sir Charles Grandison instead of Pamela to Undergraduates”, in Lisa Zunshine and Jocelyn Harris,eds.,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Novels of Samuel Richardson, New York: MLA, 2006, p.185.
[7] See Adela Pinch, Strange Fits of Passion: Epistemologies of Emotion, Hume to Aust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
[8] Ernest A.Baker,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ovel: The Novel of Sentiment and the Gothic Romance, London: Witherby, 1924, pp. 28-29.
[9] 这并非孤立现象,英国第一部小说史的作者克拉拉·里弗也曾表达过对小说的批评,认为小说不同于传奇,就是因为后者的主要特点是仿真移情,但也因为能“引发激情和虚假期待”而担不起表现“天才、品味、道德”的综合重任(see Clara Reeve, Progress of Romance and The History of Charoba, London: The Fascimile Society, 1930, p. xii)。
[10] See E. Derek Taylor, Reason and Religion in Clarissa: Samuel Richardson and the Famous Mr. Norris of Bemerton ,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p. 11. 泰勒认为理查逊深受17世纪哲学家、神职人员约翰·诺里斯所宣扬的基督教化的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塑造的克拉丽莎具有理性和禁欲的特点。
[11] See Adam Budd, “Why Clarissa Must Die”, in Eighteenth- Century Life, 31. 3 (2007), pp. 1-28.
[12] 苏珊·科恩就曾使用“novel of sensibility”一词指称18世纪小说(see Suzanne Keen,Empathy and the Novel,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4)。
[13] 这也是黄梅和耿力平的用法,不过他们并未对这个选择加以阐释(详见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1-322页;耿力平《情感小说与伦理建构——1771至1817年间的英国小说》[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章)。
[14] See Northrop Frye, “Toward Defining an Age of Sensibility”, in ELH, 23, 2 (1956), pp. 144-152, p. 149.
[15] 详见达伯霍瓦拉《性的起源》,杨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42页。
[16] Thomas Marriott, Female Conduct: Being an Essay on the Art of Pleasing, London: printed for W.Owen, 1759, p. xxv.
[17]See Thomas Marriott, Female Conduct: Being an Essay on the Art of Pleasing, pp. xvii-xviii.
[18] See James Fordyce, Sermons to Young Women, Dublin: printed for James Williams, 1767, p. 16.
[19] See Michael McKe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Domesticity Public, Private, and 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6, p. 321.
[20] See Nancy Armstrong,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8.
[21] See Thomas Laqueur,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22] See Thomas Laqueur,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pp. 10-11.
[23] See Katherine M. Quinsey , “Introduction” , in Katherine M.Quinsey, ed., Broken Boundaries:Women and Feminism in Restoration Drama,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pp. 1-10.
[24] 《克拉丽莎》的第107封信和第149封信(均出自克拉丽莎之手)中都提到过求婚的事,但是她都没有同意。
[25] See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225.
[26] Qtd. in Ioan Williams, ed., The Criticism of Henry Field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40-141.
[27]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提出婚姻应基于双方自愿和允许重组等原则,这构成了他所倡导的婚姻契约论的核心。洛克对婚姻契约的阐释与他对政治契约的重新定义相得益彰,对光荣革命后王权和政府权力的重新界定意义深远。婚姻契约在内战之前是王权论证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其基于《圣经》的永久性和丈夫绝对主权的规定被用来驳斥议会的诉求。内战之后的政治理论家们致力于对婚姻契约本身做出新的阐释,洛克从自然法的角度重新定义婚姻契约,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契约观奠定了基础(see Mary Lyndon Shanley, “Marriage Contract and Social Contrac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in Nancy J.Hirschmann and Kirstie M. McClure, eds,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Locke,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7, pp. 17-38)。
[28] See Samuel Richardson, Familiar Letters, Cambridge: Chadwyck-Healey, 1996.
[29] 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1980, p. 44.
[30] 详见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刁筱华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47-182页。
[31] 详见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第93-96页。
[32] See Daniel Rogers, Matrimoniall Honour,or the Mutuall Crowne and Comfort of Godly, Loyall, and Chaste Marriage, London:printed for Philip Nevil, 1642, p. 148.
[33] 理查逊在《克拉丽莎》第四版的后记中写道:“笔者有这样的想法:假如在这个娱乐消遣当道的时代里,他能潜入腹地,在娱乐的时髦外表下探讨基督教的伟大信条,他也就实现自己的用途了。”(R. F. Brissenden, ed., Clarissa: Preface, Hints of Prefaces, and Postscript, Los Angeles: William Andrews Clark Memorial Library, 1964,p. 351)该后记代表了理查逊对这部小说比较完善的反思。
[34] 劳伦斯·斯通《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第24页。
[35] See Amy M.Froide, Never Married:Single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 2.
[36] See Amy M Froide, Never Married:Single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158.
[37] See A Gentlewoman, The Maid’s Vindication; or, The Fifteen Comforts of Living a Single Life, London: printed for J. Rogers,1707. 类似印刷物还包括Anon., Matrimony; or, Good Advice to the Ladies to Keep Single, London:printed for T. Read, 1739。
[38] See Amy M. Froide, Never Married: Singlewome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177.
[39] Michael de Montaigne, “Of Friendship”, trans. Charles Cotton, in W. Hazlitt,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Michael de Montaigne, London: John Templeman, 1842, p. 79.
[40] 包括理查逊在内的很多男性作者对“蓝袜子”女性采取了排斥态度。理查逊就对一名单身女作者皮尔金顿(Pilkington)采取了背后贬损的态度,虽然当面还是对她有所帮助(see John A. Dussinger, ed, The Cambridge E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Richardson: Correspondence with Sarah Wescomb, Frances Grainger and Laetitia Pilkingt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lxii-lxvi)。
[41] See Mary Masters, Familiar Letters and Poems on Several Occasions, London: printed by D. Henry and R. Cave,1755; Sarah Scott, A Description of Millenium Hall, London: printed for J. Newberry ,1764.
[42] Jacques Rousseau, Julie, Or, The New Heloise: Letters of Two Lovers Who Live in a Small Town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Works, trans and eds. Philip Stewart and Jean Vaché,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7, p. 146.
[43] See Sharon Marcus, Between Women: Friendship, Desire, and Marriage in Victorian Englan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73-107.
[44] See John A.Dussinger, ed., The Cambridge E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Richardson: Correspondence with Sarah Wescomb, Frances Grainger and Laetitia Pilkington, p. 283.
[45] See John A.Dussinger, ed., The Cambridge Editions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Samuel Richardson: Correspondence with Sarah Wescomb, Frances Grainger and Laetitia Pilkington, pp. 334-346.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