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与经验主义问题
编者按
在伊格尔顿数量惊人的著述中,《批评与意识形态》以其丰富的概念术语、扎实的理论框架、严谨周全的抽象思辨和平白准确的语言建构的文本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项重大成果。与这次成功的理论创举相伴相关,书中对威廉斯身上的英国经验主义印迹进行了尖锐的揭发和批评。本文通过对伊格尔顿与经验主义问题的探究,表明伊格尔顿对自己的恩师发起经验主义批判是其文本学建构工程整体中的基础环节,也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语境有关。但是总体来看,现实关怀和政治效用是贯穿伊格尔顿学术事业的根本动机和中心路线,这个不懈坚守的中心使他能够在借用各种理论资源时,做出灵活的取舍、调整、改造乃至及时的自我检讨。无论从紧贴现实生活、追求实践成效的一贯立场来说,还是从“转向”和“回归”的表现来看,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都可以归入受经验主义影响颇多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外国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注意和思考。
作者简介
马海良,男,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英国文学。

特里·伊格尔顿
在特里·伊格尔顿迄今长达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应该是他在1976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对雷蒙德·威廉斯进行的相当严厉的批评。威廉斯是当代英国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1],是伊格尔顿在剑桥读本科和研究生时的导师以及后来的同事和战友,深受伊格尔顿爱戴。伊格尔顿的第一本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1967)特别说明是献给威廉斯的,说“没有他的友谊和帮助,就不可能完成本书” [2]。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让人想到威廉斯的经典之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二者的相似不仅在于论题的框架设置,也在于基本立场:强调个体与社会、社会与文化、各个文化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整体关系,倡导一种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积极参与、共同创造的社会主义“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威廉斯不但以其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伊格尔顿,而且其朴实宽厚、安静优雅、舒展从容、条理严谨而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也深受伊格尔顿的敬佩,后者在不少场合对老师的学问人品给予深情赞美,这与他对那些装腔作势、刻薄冷漠、自以为是而五谷不分的“牛(桥)人”(Oxbridger,牛津人、剑桥人的合称)的鄙视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仍然特别体谅威廉斯,指出他像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一样“与欧洲大陆几近隔绝,国内学术资源贫乏,除了斯大林主义和唯心主义,没有‘上层建筑理论’可资援用” [3],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批评理论的建构。不过尽管如此,伊格尔顿还是直言对威廉斯的批评,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政治改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人本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左倾利维斯主义者”等。这一举动让读者感到来得太突然,于情于理都有些措手不及。
具体来说,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在论述社会文化问题时过于倚重个体的经验或生活体验,“经验”成为威廉斯学术建树的母土,“对经验的这般坚持,对‘体验’优先的这般执着,构成了贯穿威廉斯全部著作的一个核心主旨,这是威廉斯著作的强大力量所在,同时也恰恰造成了其明显的局限。在上文中,我对自由人本主义提出质疑并对文学批评所受的影响做了简要评论,但是还未提及‘左倾利维斯主义’,而威廉斯可谓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Criticism: 28)。在伊格尔顿首创的这个“左倾利维斯主义”(Left-Leavisism)概念里,“左倾”一词似乎意在顾及威廉斯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追求,但是这个修饰语并不影响总体上把威廉斯判定为利维斯主义者,而且是其中一支的“主要代表”。这一定性定位无疑是十分严厉的,它把威廉斯排除在伊格尔顿自己所属的马克思主义队列之外,而且显示出应该从根本上清理威廉斯思想的错误的倾向。按照伊格尔顿的一贯立场,利维斯及其追随者即剑桥学派或曰“《细绎》派”是英国现代批评传统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利维斯主义的深重影响,因为利维斯主义不仅顽固地据守着英国文学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堡垒,而且广泛渗入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阵地,威廉斯可谓活生生的例子。在伊格尔顿的举证中,威廉斯与利维斯主义的关键联结点是对“经验”的先验式推崇,“《细绎》所标举的‘实用批评’集中体现了一种幼稚的感性的经验主义,它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用生活经验的直接性来验证各种美学范畴。这种将普遍性溶解于‘体验’之中的方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像艾略特将意义的关联拆解成诗歌的具体之物一样突出”(Criticism: 15)。如果说从更大的历史维度看,利维斯主义延续了经验主义的英国思想传统,“左倾利维斯主义者”威廉斯自然也无法脱离这条传统之链,伊格尔顿对这一关系脉络讲得非常清楚而明确:“这种人所共知的英国式经验主义经过《细绎》,成为贯穿威廉斯著作的主动脉,这一点就从他对大卫·休谟的特别崇敬中也能看得出来。”(Criticism: 23)

雷蒙德·威廉斯
尽管伊格尔顿对威廉斯和利维斯主义以及整个英国批评传统作了深入挖掘和猛烈批判,但是《批评与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在于提出一套有效可行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结果显示伊格尔顿不负众望,通过文学生产方式(literary mode of production)、一般意识形态(general ideology)、作者意识形态(authorial ideology)、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文本生产(textual production)、文本意识形态(textual ideology)、意识形态生产(ideological production)等一系列经过特殊界定的概念,建构起以“文本学”(science of text)为主体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次重大创举。
《批评与意识形态》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尔图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启发,对此伊格尔顿本人也坦然承认。然而,伊格尔顿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学术方向,重新强调文学和文化理论的政治本质和功能,主张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采取积极主动的阅读方法,在文本中发掘和注入有助于当下政治实践的各种意义,而不是拘泥于“科学的”客观、精确、严密。作为这次“转向”的路标,《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1981)从阿尔图塞的资源转向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方法。本雅明的启示是,“历史”的价值在于现在,是过往“记忆”在当下“紧急关头”激发出来的对未来的启示和顿悟。要让逝者得到安慰和安息,不让悲剧重演,就必须全力击破已经板结的历史,在“往事”的废墟里种下未来的希望之树。如果说本雅明提供了历史哲学的一般启示,那么伊格尔顿从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和舞台实践中得到的是一种具体的文学批评的可能性:文学读者并不是只能像传统的戏剧观众一样做“受众”——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入,而是可以像布莱希特的观众一样审验剧本,甚至可以参与创作出各种潜在的文化剧本。据此,伊格尔顿提出了革命批评的几项重要任务及方法策略:“第一,通过已经转换了的‘文化’媒介,参与作品和事件的生产,为了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效果而将‘现实’虚构化。第二,作为批评家,应该暴露非社会主义作品的修辞结构及其产生的不良效果,以此与现在已经很少被人提及的‘虚假意识’做斗争。第三,对这些作品进行尽可能‘格格不入’的阐释,以占用对社会主义有价值的一切资源。简言之,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实践是投入型的、论战型的和占用型的。” [4] 这种典型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伊格尔顿后来的直至今日的学术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本雅明与布莱希特,摄于斯文堡(1934年)
《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所体现的从阿尔图塞朝向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调整转变很容易让人理解为向威廉斯路线的“回归”,这样的看法似乎也能获得伊格尔顿本人的认可。他在1989年怀念威廉斯的文章中写道:“他仍然待在那里,胸有成竹地等着我们,直到我们当中一些较年轻的理论家们更悲哀也更明智地最终从那几条死胡同里折返回来,在我们曾经离开他的地方重新和他站在一起。”[5] 在远处绕了一圈之后折返回来的伊格尔顿,由衷地敬佩威廉斯的学术眼光和思想高度,甚至对威廉斯的政治地位也作了重新认定:“威廉斯一生的突出之处是他稳步不断地走向政治左派”,甚至“比马克思主义者们更像马克思”(《历》:235)。
伊格尔顿当年对老师威廉斯的严厉批评由后来的伊格尔顿本人做了检讨和纠正,但是他的自我批评似乎更多地坐实了“草率”、“刻薄”、“错误”等个人历史问题,对于反对者们来说,甚至他的“迷途知返”也可能在可信度上大打折扣。然而人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至少就伊格尔顿的情况来看,那条“死胡同”并非黑暗一片或死路一条,并非毫无价值或不能改造利用,他与威廉斯的牢固关系不仅具有长期师生情谊的深厚基础,而且得到共同的学术伦理的有力支撑,即以真诚面对真理。这一切在他怀念威廉斯时所做的特别注释中得到了简洁而清楚的说明:

也许应该在此解释几句。我无意暗示这个阶段所有的理论发展都一概走入了死胡同。威廉斯本人尽管尖锐地批评了其中的一些理论,但也吸收了另外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空前繁荣,尽管他自己的作品与某些时潮相冲突,但是仍然受益于这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繁荣,我以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情。我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对威廉斯的批判就萌生于那些新潮流,有人觉得我不应该那样做,甚至有点不光彩。威廉斯却绝不这样想。他尽管对我的一些批评保留异议,但对另外一些批评却是认可的,这是一位其著述不断进化的思想家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反应。他自己也能对自己早期的一些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他欢迎热烈的论争,而不是驯顺听话的弟子。有些人当时就为他奋起打抱不平,现在仍有人这样做;这样做也许与他更为隐忍的自我批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我仍然为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对威廉斯的许多批评观点辩护,当然,如果是今天的我,将会以一种更和煦的风格和一种不同的语气提出自己的批评。对我而言,他的著作无比重要,当我竭力与这样的著作保持一定的批评距离时,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眼界狭窄的话,惹人嫌恶,对此我十分抱歉。(《历》:262)

可以看出,“反复”并非伊格尔顿个人的“问题性格”及其表现,更不能描述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实际情形,即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这个个案上,伊格尔顿也并没有撤回自己的主要观点,而是在回到威廉斯身边时“仍然为自己在《批评与意识形态》里对威廉斯的许多批评观点辩护”;在1996年初版、后来多次再版的他本人与弥尔纳(Drew Milne)合编的读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一章《文本学》赫然在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本雅明、布莱希特、考德威尔、卢卡奇、阿多诺、阿尔图塞、威廉斯等人的篇章放在一起,足以表明伊格尔顿坚持认为自己在离开威廉斯的那段时间拿出了一个最有分量的东西。这个自我评估其实不无道理,整整40年后的今天再读《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初版,仍然能看到它所以持久不衰的独特价值。撇去“年轻人常有的急躁”(《历》:258),撇开对威廉斯的某些误判,《批评与意识形态》堪称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用一套齐全的专门概念和术语对唯物主义文学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严密精细的表述,尤其是文本学的建构为马克思主义批评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方法。只能大而化之地从“文学外部”谈论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所谓文本生成条件,不善于对文本本身做细密的阅读分析,不能揭示文学作品内在的审美品质,终究属于外行所为,这些说辞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话语中最为常见,而让这类批评显得底气十足的证据是各种有能力审美的文学理论所设计的分析程序,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阅读法、新批评派的细读法、热奈特叙事学开发的“工具箱”等等。现在,伊格尔顿的文本学拿出来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范畴工具,让人们能够期待马克思主义批评完全可以对文本形式做确切而透彻的分析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伊格尔顿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处空白。
因此,我们很难说伊格尔顿的这次回转属于那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幡然悔悟,与昨日之旧我的彻底决裂,更不能简单地以为他转而拥抱经验主义,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事实上,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依然对经验主义时有批评,一如他仍然坚持对利维斯主义的批判。就在标志其转向的重要著作《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里,伊格尔顿仍然把经验主义与利维斯主义绑在一起,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十七世纪悲苦剧(Trauerspiel)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对十七世纪英国诗歌的解读进行对照,指出利维斯们的“伟大传统”对“有机性”的膜拜与十七世纪英国统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同样,伊格尔顿并没有完全撤销他关于威廉斯曾经受到利维斯主义影响的看法,就在前引那篇怀念威廉斯的文章里,他仍然说:“主持《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杂志时的早期威廉斯信奉左倾改良主义或左倾利维斯主义。”(《历》:260)最有力的证明也许就来自前文所引的“他自己[威廉斯]也能对自己早期的一些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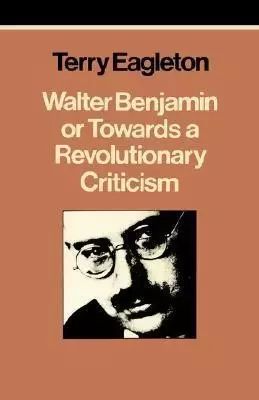
伊格尔顿《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我们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来了解伊格尔顿“反复”转向的历史成因和内在逻辑,从而准确地理解伊格尔顿学术思想的突出品质,并且通过检索伊格尔顿的学术路径,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文化理论的发展获得某种整体性的把握。
显然,首先还得回到“经验”问题。根据威廉斯的考证,“经验”(empiric,empirical)一词于十六世纪进入英语,意指与医学研究相关的“试验”或“实验”,后来这一概念广泛用于其他领域,但其基本含义仍然与“实验”相关,意思是通过对真实事件的具体观察,在充分总结经过试验和实验的过往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或可靠知识。十七世纪出现了“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词,意指在哲学高度上坚持知识源于感官体验,即经验:“知识理论中出现的各种具体而复杂的论述产生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性用法,即用‘英国经验主义’来指称从洛克到休谟等人的哲学思想。”[6] 从威廉斯的考据中可以清楚看到,“经验”是经验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在英国学术背景下使用“经验”概念,尤其是强调经验的优先性,就是表现出经验主义的思想和立场。经验主义由于容纳了众多哲学家、思想家的成果,自然论述纷杂,体系多元,其中不无相互对立的命题,但是总体而言,都把对事物对象的直接感知或经验看作一切知识的起点和来源。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等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把经验尊奉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放弃了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从而获得正确认知的人的天赋理性能力,实在不可思议。感觉、体验、经验并非人类所专有,甚至在经验基础上展开的联想也非人类特有的禀赋,“动物的联想与单纯的经验主义者的联想一样,他们以为凡是以前发生的事情,以后在他们觉得相似的场合也还会发生,而不能判断同样的理由是否依然存在” [7]。可是对于一代又一代的英国经验主义者来说,人一生下来,头脑中就储存着一套“先验的”(先于经验的)基本观念因子和理性能力,只要按照理性和逻辑法则启动这些天赋因子,就能产生出知识和真理,理性主义者的上述说法同样是匪夷所思的。总之,英国经验主义沿着自身的轨迹向前运行,沿途竖立起来的“习俗”、“常识”、“联想”、“想象”等重要路牌成为英国学术话语传统中的几个特色关键词。
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经验主义主要是一种认识论。但是对于伊格尔顿来说,经验主义不只是一些哲学家个人对获得可靠知识的可行方法进行的探索和尝试,而且还是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阶级利益诉求和政治目标的英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确,当“经验”演化成“习俗”和“传统”并进一步等同于“有机性”时,就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英国特色”了。利维斯的批评思想被伊格尔顿称为“《细绎》意识形态”(the Scrutiny ideology),实际上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本主义(liberal humanism),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矛盾体。英国小资产阶级群体处于历史的边缘,但是在精神上以中心自居,于是把自己设想成社会的精英、传统的卫士,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紧抱前资本主义的“有机过去”的真相所在。他们追随阿诺德,坚守文化的精神高地,实质上也是为了填补宗教失势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空白。当然,利维斯主义者们讨厌“意识形态”这个词,只是在伊格尔顿看来,“为了抗击意识形态,《细绎》诉诸‘经验’,好像‘经验’真的就不是意识形态的沃土”(Criticism: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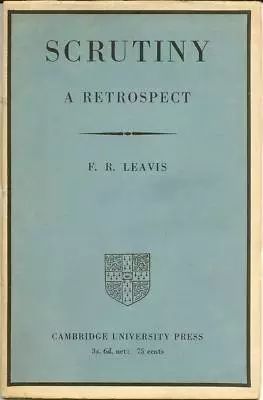
利维斯主编的《细绎》
炮口对准经验主义,伊格尔顿并不是孤身作战。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英国学界兴起了一场批判经验主义的热潮,而且主要论争发生在左派内部。佩里·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1964年第1期发表《目前危机的根源》,指出英国的现实困境和各种问题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归因于经验主义。[8] 紧接着在第2期上,杂志编者之一奈恩以《英国工人阶级》一文进行呼应,把经验主义称为“英国的民族文化”,并认为正是这样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造成了英国的“封闭、落后、守旧、迷信”等问题 [9]。安德森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英国民族文化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贵族阶级将传统主义和经验主义结合在一起” [10]。在年轻激进知识分子发起的经验主义批判中,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等上一代左派学者也成了靶子。
发起经验主义批判的本土原因是左派以及新左派与自由人本主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导致英国的左派力量在激荡西方世界的学生文化革命、女权运动和遍及世界的殖民地解放运动浪潮中显得异常落伍、沉寂和孱弱,深受经验主义影响的激进话语失去了对社会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力量。经验主义批判的直接触发点是阿尔图塞理论的发现和引入。阿尔图塞用结构主义理论来阐释马克思主义,他提出的社会形态结构论、多元决定论、话语实践论、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论,似乎都为一海之隔的英国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打开了一扇别有天地的窗户。多元决定论为解决长期困惑左派的简单粗糙的经验决定论和镜像式反映论展示出新的可能性,使他们可以摆脱陈旧且往往无力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解释模式的束缚;社会形态结构论对于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肌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解释;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论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推动对资产阶级统治意识和话语体系的揭露和批判;而话语实践论则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专业自信注入了动力。于是,出现了伊格尔顿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1970年代的空前繁荣”,以及伊斯托普等人所确认的“1974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达到了巅峰” [11]。具体表征就是阿尔图塞理论成为影响力最大的话语系统,“在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早期,整个人文科学都受到来自阿尔图塞的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和影响” [12]。尤其是年轻学者,纷纷走向阿尔图塞,推出了大量受阿尔图塞理论影响的学术著作,甚至出现了集中新学成果的专门刊物,例如非常活跃的《荧屏》(Screen)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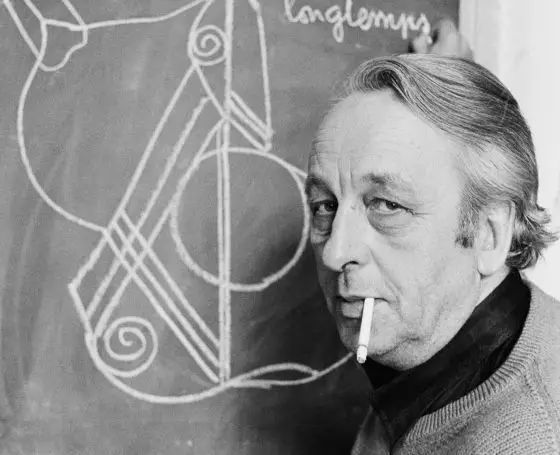
路易·阿尔图塞
英国左派内部的论争有时也被简化说成“理论”与“经验”之争。按照阿尔图塞的阐述,知识并不是头脑对外在客观实在世界的反映,真理并不是存在于外部世界某个地方并等待人的意识去“切中”(treffen)、发现和取来的一种实体,“只有经验主义才会以为,文本与历史之间存在着自发的直接的关联,应该抛弃这种幼稚的观念了”(Criticism: 70)。知识其实是理性思辨和话语过程的一种结果,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形式,因此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过程,具有生产性,“我们必须抛弃那种直接反映和读解的镜像关系的神话,而是应该把知识理解为一种生产过程” [13]。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国知识界还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满足于描述自己的琐碎经验,拒绝通过理论思辨获得对世界的总体把握。正如威廉斯自己十分清楚的那样,经验主义者的共性是“倚重观察和通行的做法,而对理论解释持怀疑态度” [14]。而奈恩则有些激愤地说:“英国经验主义对理论有一种发自本能的排斥。” [15] 反经验主义者的“情感结构”也可以概括为对“理论”本身的热烈推崇,甚至就像伊格尔顿的同代人亨戴斯和赫斯特那样,高调表达对经验主义和实证方法的不屑一顾:“我们的建构和提出的论点是在理论层面上进行的,是依赖所谓历史‘事实’的经验主义者无法辩驳的。” [16] 这种理论激情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不过对于伊格尔顿来说,“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意识形态批判力量,还因为它具有切实的不可替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效用:“真实是经验所无法感知的,它必须把自身隐藏在现象范畴之中(商品、工资关系、交换价值等等),让人们仅仅看到这些范畴。”(Criticism: 69)也就是说,理论是正确认识世界和切近现实的有效途径。
多种因素合力使经验主义批判成为《批评与意识形态》立论的反证支点,成为文本学工程的前期准备和起点,成为这部里程碑著作中的第一章。从写作策略和效果的角度看,把威廉斯置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甚至利维斯主义范畴内加以审查,应该可以增强全书的论述力量。
经验主义批判构成了《批评与意识形态》理论成就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项突出成就与其说是汲取了阿尔图塞的理论资源,不如说是对阿尔图塞理论进行大力改造的结果;该书引人注目的地方更多在于与阿尔图塞理论的差异,例如对“生产方式”概念的运用。阿尔图塞虽然把物质的经济的生产方式放在终极决定因素的位置,但那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并不具有实际效用,因为他提出多元决定论和多重实践论的一个原初动机,就是为了剥离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范畴对精神和话语实践的形影不离的沉重压制。而在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架构中,“生产方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因而能够进一步提出“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相应衍生出一般生产关系和文学生产关系以及文学生产、文本生产、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生产等注入新意的概念。这样一种关联使文学文本的生产以及解读与社会历史的物质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以此与阿尔图塞更加突出话语行为本身的自主性和实践性的观点拉开了距离,符合马克思经典中对物质与精神关系的论述。再如“意识形态”,阿尔图塞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此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知识或理论的科学方法,才能揭示意识形态的遮蔽性。相比之下,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并非完全虚假之物,它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因此文学文本中呈现的意识形态虽然与历史真实隔了两层,但是并不妨碍通过具体的分析,能够解读出背后的历史真相;再者,构成文本的意识形态生产本身是一个真实的过程。此外,伊格尔顿对价值判断的坚持、对读者能动性的重视、对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的强调,也不在阿尔图塞的理论议程之内。

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
1986年,《批评与意识形态》出版十年之后,已经“更弦易辙”的伊格尔顿可以“平静下来回顾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审视自己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冷静公允地评价阿尔图塞理论。他的总体看法是,阿尔图塞提出的所有理论概念都击中了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暴露出来的软肋,包括庸俗的历史目的论、同质化的历史观、幼稚的理论与实践匹配论、存在主义式的主体论等等。然而阿尔图塞提出的解决之道却带来了新的严重问题,“理论”成了超验的东西,“理论实践”实际上完全失去了现实作为的能力,成了封闭的话语循环,完全消除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整体性,只剩下一些散碎的偶然的随机聚合,而主体消解的严重后果是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可能性(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中指出,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 [17] )。当伊格尔顿发现阿尔图塞理论实际上无法解决既有问题,而且还会产生新的问题之后,他转身寻求新的途径,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历史语境的还原固然可以为今天“理解”伊格尔顿的阿尔图塞转向提供一些重要线索,但是这种体谅式的理解不足以解释他随后的文化政治转向或向着威廉斯的回归,也难以解释这一事实:伊格尔顿后来对阿尔图塞理论的清醒反思其实在当年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或者说他在批评威廉斯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持了与文化唯物主义的割不断的牵连。总之,伊格尔顿与阿尔图塞的种种差异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那些重要差异而打通了“死胡同”,相当成功地建构了唯物主义文本学,绝不是缘于运气。
细察可见,伊格尔顿的“反复”表象下有一条始终坚持的主线,也可以说,他的“反复”本身是不懈持守某种根本立场的合乎逻辑的反映。伊格尔顿著作中广泛而及时地征用各种理论体系的语汇,包括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用语,但他经常申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坚持使用马克思原典中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展开论述,彰显自己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例如他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生产方式范畴和意识形态概念的论述,这样的原汁原味即使在激进阵营里也显得十分突出。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曾经让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困惑,花费了许多笔墨来厘清这一对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些理论家试图采用其他阐释模式来化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理论难题,例如威廉斯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公式是抽象的,无法有效地说明丰富复杂的现实状况,应该通过“实际经验”、“整个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等范畴来认识现实。阿尔图塞也是在某种意义上通过意识形态理论来消解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难题。而伊格尔顿无论靠近阿尔图塞,还是回到威廉斯,抑或吸纳后结构主义的某些用语,始终没有放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然而把生产方式与文学和艺术关联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似乎并不那么顺利,要么走上庸俗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小路,要么使审美消失于社会学的阔大领域。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生产方式”概念,把向来视为精神现象的文学与物质活动的生产方式关联起来,通过对“文学生产”机制和过程的细致分析,阐明了蕴含于艺术形式和审美活动中的物质性,这一创举相当成功地使精神活动与物质过程统一起来,解决了某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活动的实践性具有了真正坚实的基础,可以更好地释放艺术实践的能动和创造力量。从马克思的著作开始,“意识形态”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而且经过长期发展,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成为标志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意识形态批判是人类解放工程的一部分,因此他在意识形态议题上一直用力尤深。他于1991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导论》(Ideology: An Introduction)对这个概念的历史谱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一些重大争论;1994年,他又为朗曼出版公司编辑了《意识形态读本》(Ideology),突出表明他对这个范畴的高度重视。他的意识形态研究成就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破除了对意识形态的诸多片面刻板的理解,譬如与包括阿尔图塞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他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特定人群的症状,而是所有人意识中都存在着的一种形态;二、对意识形态的结构作了具体深入的阐发,描述了包括一般意识形态、各种局部意识形态、个人意识形态等层面的意识形态结构;三、以“意识形态生产”为核心建构了文本学,对“审美意识形态”范畴作了系统的阐发。

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导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8] 马克思的这句话是伊格尔顿经常引用、念兹在兹的座右铭。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折中余地的守护已经超越了学术兴趣的范畴,进入一种信念甚至信仰的境界,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解释世界的最好理论,更是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是精神批判的利器,更是把美好生活从想象和设想变为现实的可靠路径。简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在于政治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以“伊格尔顿式”的机智说:“马克思更像一个反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Why: 130)政治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进行的各种话语和行为实践,在阶级社会里,群体利益往往呈现为不同阶级的特殊诉求,因此必然地表现为各个阶级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取向上的差异、对立、冲突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就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进入所有人按照审美理想达到自我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此,早在学生时期,伊格尔顿就积极地投身于激进政治活动,或参与政治集会,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他最早参加的一个校外活动集体叫作“十二月小组”(the December Group),这个英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创办了机关刊物《倾斜》(Slant),伊格尔顿主持过该刊1969-1970年度的活动。[19] 他的理论作为也往往受到现实政治动向的触动和影响。《批评与意识形态》所表现的理论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年里的政治现实的变化密切相关。1974年2月,英国煤矿工人宣布开始总罢工,得到其他行业工人的热烈响应,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对策是解散内阁,提前举行大选,这是一场事关“到底是谁领导英国”的对决,堪称宪章运动以来最大的工人运动。虽然英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由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承诺兑现,毕竟标示了工人阶级取得了现实的胜利。

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摄于唐卡斯特(1974年)
激进运动的新形势鼓舞了左派知识分子的社会信心,同时也召唤他们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做出科学可靠的论述。因此应该说,即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时期,伊格尔顿空前投入理论,其动力和归宿仍然主要在于现实的政治效用。他在1986年的一次访谈中证实:“我当时属于年轻一代社会主义者,我觉得以威廉斯为代表的上一代新左派既缺乏理论严密性,也缺乏政治热情。” [20] 如此看来,当时他对威廉斯进行的俄狄浦斯式清算可能并不是因为威廉斯在认识论上的偏执,也不是他对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忽视,甚至不完全是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理论模式的质疑,而是因为威廉斯最终失去了政治的锋芒。进一步看,让伊格尔顿真正恼火的可能是威廉斯对“阶级”的漠视,后者认为“实际上并不存在阶级,只存在把人们看作阶级的各种方式而已……我们只是把一群个体划分为这样那样的阶级、国族或种族,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单个地看待个人” [21],阶级竟然成了一种因人而异的主观感觉,一种可以替换的“看”事物的方式,一个漂浮的能指,这是始终把政治追求放在首位、把社会革命的有生力量寄托于工人阶级的伊格尔顿断然不能接受的。其实,他对威廉斯的所有批评都可以归结为威廉斯思想放弃了主动介入政治实践的意愿,使批评理论成为纯精神的、文化的或唯心的活动。
伊格尔顿于1980年代连续问世的几部著作大声呼唤文化工作者的政治作为,实属保守的撒切尔-里根主义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再次滑入低潮时的奋起一搏之为。进入1990年代以来,他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不断加码,这是因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文化相对主义盛行,其实质是为商品的任性流通消除一切障碍;如此这般的文化相对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绝对主义或唯文化论(culturalism),因为它把物质的社会结构替换成观念的转换。无论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绝对主义,它们的症结都在于有意无意地掩盖了现实的真实状况,其后果是拆除了政治革命的引信。可是,源于经济利益的文化冲突每天都在真实地暴烈地发生着,进行着,因此伊格尔顿特别提醒激进知识分子,不要被时髦的后现代辞令迷住了双眼而丧失政治活力,“今天,像斯坦利·费什的那种唯文化论或唯习俗论是要把左派的认识论轭制在保守政治之下,正如理查德·罗蒂要把它套在自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里面” [22]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伊格尔顿日益关注民族主义议题,这不仅是因为爱尔兰与英国、爱尔兰与他一家人之间的特殊的历史纠葛,还因为他的政治日程及时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和族群冲突不断增加的现实局面。

伊格尔顿《爱尔兰的真相》
伊格尔顿向来明确的政治诉求也可以从他的写作风格里得到有力佐证。他的语言直截了当、晓畅明了,与常见的那种晦涩重拙的文论形成鲜明对照,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的理论探讨总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现实的日常生动性和真切感受使他能够用平常通俗的语言说清楚事理真相,而不是只有借助于一套现成的理论术语,才能进行表达;另一方面,强烈的政治效用目标让他有意识地追求受众的最大化,因此他会大量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其中最常用的是“比喻”,因为比喻可以使抽象的思想变得形象具体,容易理解。这种可以称为“伊格尔顿体”(Eagletonism)的文章品质是伊格尔顿本人自觉塑造的结果,他属于那种少见的具有强烈风格意识的理论家,他明确主张学术阐发也应该尽量贴近普通语言,“有些牛津哲学家们非常热爱‘普通语言’这个概念,但是牛津哲学家们的普通语言却与格拉斯哥码头工人的普通语言几无共同之处” [23] 。事实表明,伊格尔顿的语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他的著作很多都能像畅销书一样广为流传,以《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1983)为例,其读者范围远远超出了文学专业的学生,世界主要语言都有该书的译本。伊格尔顿体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论战风格,他不仅在批驳敌手时摆出嬉笑怒骂、不依不饶的论战姿态,即使面对同志时,他的批评也往往让人有过于直率之感,不过如果知道伊格尔顿曾经这样批评詹姆逊,“他绝不是一位论战或讽刺作家,可是在我看来,这是政治革命者的根本模式” [24],那么就会理解《批评与意识形态》不仅对威廉斯的经验主义倾向不满,也对他的写作风格颇有微词,是因为与威廉斯“四平八稳、全无棱角”(Criticism: 22)的风格相对照,伊格尔顿那火辣辣的文笔能够更加快捷有效地传达作者的政治意图,激发读者的政治激情,在二者的生动交流中实现文化行为的政治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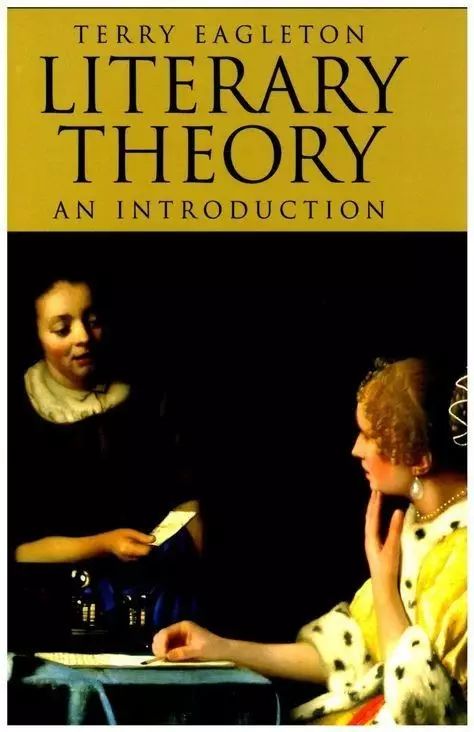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谈到思想观念的生成方式时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25] 伊格尔顿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毫不迟疑的政治追求,说到底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源于他忠实于真切的生活体验的学术精神;这样的学术情怀外化扩展为让所有人过上美好生活的赤热愿望。换言之,他的政治取向和理论选择与实际生活的关系不是“从天国降到人间”,而是相反,正如他所说,“人们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绝不仅仅因为他或她信服了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或被马克思的经济学算式的说服力所打动。最终而言,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唯一原因是他反对历史中绝大多数男男女女一直过着痛苦而低下的生活,他相信这种状况在将来是可以改变的” [26] 。他在谈到威廉斯当年的学术条件和背景时说:“他是一位威尔士工人阶级父母的儿子,从一个异常封闭的农村社区进入剑桥大学,阶级、文化、政治以及教育等等问题是自发地摆在他面前的,这些问题是与他的家庭出身和个体身份密切相关的。”(Criticism: 24)伊格尔顿也是出身于地道的工人家庭,不同在于他祖父那一辈是从爱尔兰移民到曼彻斯特的,而且父辈们也许因是爱尔兰人遭受过英格兰人更严酷的压迫而更加容易安于社会边缘,伊格尔顿的父亲特别木讷,好像把所有言说的机会都让渡给了儿子,或者说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如果威廉斯的个人实际经历和体验是其思想力量的活水源头,那么伊格尔顿思想历程中出现的变与不变,又何尝不是其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的忠实表现呢?
“从人间升到天国”,即以实际活动中的人为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真正理解人的正确路向,在认识论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样,伊格尔顿也是把人的实际生活境况与这个人的认识论倾向关联起来,而且可能由于自己的阶级出身,他认为那些卑微者、属下者、劳力者往往更容易按照唯物主义原则认识世界,“那些来自社会边缘的人们一般不会成为理性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不会夸大思想观念的作用” [27] 。伊格尔顿著作中不乏认识论的阐述,甚至从认识论的第一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开始:“意识就像儿童的理性一样,总是‘姗姗来迟’。甚至在我们开始反思之前,我们就总是已经处于某种物质环境中,而我们的思想无论多么抽象,多么理论,都不可能违背这一基本事实。只有那种唯心主义哲学才会忘记人类的思想基石在于实践。如果把思想观念从这个环境中剥离出来,就可能真的误以为是思想创造了现实。”(Why: 136)这里描述的意识、观念、思想、理论,概言之精神的生成路线,完全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更进一步,明确地把“现实生活”与个体的实际经验和直接体验联结起来,甚至把作为知识之源的这种经验或体验与最为个体化的“身体”紧紧捆在一起:“我们人类具有认知能力,是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身……可以首先这么说吧,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由我们的身体需要决定的。”(Why: 145)身体进入了伊格尔顿的认识论范畴,而且以其坚实的物质性成为知识的可靠起点,因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通过感觉进行体验和作用于世界的,感觉是个体自我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媒质。当然,伊格尔顿把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这种基础地位再次归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马克思把人的感觉看做积极投入现实的形式”(Why: 136)。
当感觉、体验以至身体成为伊格尔顿知识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基础概念时,确实可以说他随着“经验”回到了威廉斯。如果伊格尔顿现在认为个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清楚了,马克思对个体坚信不疑,对抽象教条深感怀疑”(Why: 238),那么就不能把威廉斯对个体经验的重视看作经验主义。这两个判断显然是互相矛盾的,除非伊格尔顿把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让二者互为兼容。乍看之下,这确实是个比较棘手的难题,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本身,即非此即彼、浮浅简单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按照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伊格尔顿反对经验主义,就等于赞同理性主义;当他说“来自社会边缘的人们一般不会成为理性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时,就是在赞同经验主义并且把经验主义看作一种唯物主义。如此演绎,顶多只能抓住一些形式皮毛,漏掉实质的内容。思想过程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因此对思想形态的解读必须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如前所述,《批评与意识形态》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是197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所激发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批判经验主义的集体行为中,伊格尔顿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经验主义可能带来的保守的政治后果,而不是像阿尔图塞那样通过批判经验主义认识论来铺设立论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与其他人类思想完全隔断从而纯粹地自生自长的封闭空间,而是充分吸收消化各种文化成果的“合理内核”,因而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主义”和理论发生各种交集或融合,这个事实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丰富的例证。经验主义就属于这种情况。至少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在诸多概念和命题上存在着明显的相通之处。由于这个缘故,伊格尔顿可以频繁而自如地把现实生活、个体经验、身体感觉、社会实践放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整体中调度使用;也是在这同一个层面上,伊格尔顿指出,为未来的美好社会而打拼的革命者并非一群脱离实际的“梦中人”,“其实,革命者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现实主义者” [28]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经验主义可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它们是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体系,而且关键是,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经验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二者互为条件;伊格尔顿对此十分清楚,他用力强调的身体是与社会生产相联系的物质的身体,而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生理的身体,“对于马克思来说,我们的思想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这是由我们的身体需要所决定的一种物质必然性……意识是我们自身与周围物质环境进行互动的结果”(Why: 135)。身体的功能意义在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等范畴联系在一起时,才能得到阐明。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
换个角度看,即使伊格尔顿的政治身份和思想立场都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不妨说,他也未免于经验主义的影响,一如考德威尔、威廉斯、汤普森、霍加特等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身上显示出集体性的经验主义印记。如果像学界普遍认同的那样,英国马克思主义应该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以示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特色,那么坚持文化政治批评的伊格尔顿可以通过“文化”标签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福焉祸焉,英国马克思主义注定无法剔除经验主义的印迹,正如某种程度上,受经验主义缠绕恐怕是所有英国人难以跳出的文化宿命。但就如威廉斯所说,“当[经验倾向和经验主义]这些词语用来形容国民性时,譬如‘英国人的经验主义倾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顽固经验’,那就有失严肃了” [29] 。注重个体经验之具体、多样、丰富的威廉斯反对给英国人贴上“经验主义”的集体标签,认为那样做过于笼统,过于抽象,有违真实(殊不知,经验主义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重视个体经验)。实事求是地讲,威廉斯的说法并不能降低经验主义对于英国这一方水土及其人民的重大意义。从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贝克莱等人建构的主体工程,到夏夫兹伯里、伯克、边沁、穆勒甚至阿诺德等人所做的不断拓展,以至二十世纪英国思想家们的传承光大,经验主义可以说成了英国人的文化胎记。其实,英国人实在有理由这样抱持经验主义,因为社会史和思想史都已经充分证明,如果没有经验主义,英国不可能率先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不可能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可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按照伊格尔顿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创造的巨大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财富是保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顺着这一逻辑,经验主义影响英国马克思主义,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一现象至少提示我们,学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在根本上都是本土历史和现实的产物,伊格尔顿也未能例外,而且十有八九是出于清醒自觉的选择。
[1] 威廉斯虽然没有像伊格尔顿那样在很多场合特别申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他从未宣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但是实际上,威廉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尽管后来由于违背英共政策,执意入伍参加二战而自动脱党。威廉斯的学术工作一直是围绕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因此他被广泛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
[2] Terry Eagleton, Shakespeare and Society: Critical Studie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0, p. I.
[3]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Verso, 1976, p. 2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1, p. 113.
[5]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6]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1983, p. 116.
[7] 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上册),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页。
[8]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in New Left Review, No. 2 (1964), pp. 85-86.
[9] See Tom Nair,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in New Left Review, No. 24 (1964), p. 52.
[10] Perry Anderson,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New Left Review, No. 50 (1968), p. 12.
[11] See Antony Easthope,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
[12] Antony Easthope,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 p.xiii.
[13]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 trans. Ben Brewste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p. 24.
[14]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115.
[15] Qtd. in Antony Easthope, 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 p.1.
[16] Barry Hindess and Paul Hirst, 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75, p. 3.
[17] See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6页。
[19] See Elaine Treharne and Stephen Regan, eds. , The 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vol.1,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1, pp. 211-212.
[20] Andrew Martin, “Interview with Terry Eagleton”, in Social Text, 13/14 (Winter/Spring,1986), p. 85.
[21]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 Wintus, 1961, p. 96.
[22] Terry Eaglet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8, No. 1 (1977), p. 2.
[23]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p. 4.
[24] Terry Eagleton, Against the Grain, London: Verso, 1986, p. 71.
[25]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收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2页。
[26]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p. 96.
[27] 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A Memoir,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 2001, p. 56.
[28] Terry Eagleton, The Gatekeeper: A Memoir, p. 85.
[29]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117.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