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道德、政治 ——读伊格尔顿的《圣奥斯卡》
编者按
当代英国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受到普遍关注,但他的文学创作较少为人注意。本文以伊格尔顿重要戏剧作品《圣奥斯卡》为研究对象,展示伊格尔顿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同时力图揭示这一作品(及其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与伊格尔顿文学思想之间的联系。
作者简介
耿幼壮,男,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

特里·伊格尔顿
由斯蒂芬·里根选编的《伊格尔顿读本》(The Eagleton Reader)于1998年出版,其中收录的最后一篇文字是一首小诗,或更准确地说,是一支谣曲(ballad),题作《马克思主义批评谣曲(调寄辛纳屈父女所唱〈蠢事〉)》(“The Ballad of Marxist Criticism,to the tune of‘Something Stupid’by Nancy and Frank Sinatra”)。如标题所示,伊格尔顿的这支谣曲借用了《蠢事》的曲调,但二者在内容上也并非全无联系。我们知道,流行音乐大师辛纳屈和其女南希演唱的这首传世名曲讲述了一位恋人对爱情的苦苦寻觅,而伊格尔顿创作的这首诙谐小诗也表达了一位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懈追求。在里根看来,这本厚重的《伊格尔顿读本》用《马克思主义批评谣曲》作结再为合适不过。因为,伊格尔顿对政治讽刺诗歌和谣曲的偏爱说明了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明显倾向:将批评与创作、理论与通俗文化、意识形态与艺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里根认为,伊格尔顿为自己的戏剧集《圣奥斯卡和其他剧作》(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所撰写的引言最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1] 在那篇引言中,伊格尔顿声称:批评和理论文字本身就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反之亦然),而他引证的权威就是其最喜爱的作家奥斯卡·王尔德。[2]
在我看来,在伊格尔顿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中,《圣奥斯卡》是最为成功也最值得关注的作品。这部戏剧以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为主角,以英国文学史上那件引人注目的“道德丑闻”为背景,却格外醒目地使用了“圣奥斯卡”这一名称。在戏剧形式上,《圣奥斯卡》显然对布莱希特有所借鉴,这清楚不过地表现在剧中使用的歌队和穿插其中的谣曲上。在语言风格上,伊格尔顿追随的对象则是王尔德,那是一种尖锐、嘲讽、轻松、机智的语言。不过,若要理解《圣奥斯卡》这出戏剧对于王尔德这一人物的刻画与呈现,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伊格尔顿本人视域广阔的文化-理论关注,其中当然包括他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事实也是如此,伊格尔顿在其中期以后的著述中就不断谈及王尔德,而《圣奥斯卡》的首演与伊格尔顿选编的《王尔德戏剧、诗文集》(Oscar Wilde:Plays,Prose Writings and Poems)的出版几乎同时。戴维·阿德逊甚至认为:“伊格尔顿对于王尔德的介入在许多方面,即使不是在所有方面,都等同于其对后现代主义的不断介入。”[3] 这一看法可以自伊格尔顿本人那里得到证明。在《圣奥斯卡》的前言中,伊格尔顿讲述了他创作这部戏剧的缘起。在他列举的几点中,首先就是对于许多人不知道王尔德是爱尔兰人的不满,或者说,是对不列颠文化帝国主义的不满,而这种情绪在伊格尔顿撰写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中不断得到抒发。其次,伊格尔顿惊喜地在王尔德的著作中看到了许多当代文化理论洞见的预示,诸如:“……作为自我指涉的语言,作为信手虚构(a convenient fiction)的真实,作为矛盾体和解构体的人类主体,作为一种‘创造性’写作形式的批评,以及与伪善意识形态相对抗的身体及其愉悦。”[4] 这使他想到了巴尔特和尼采,并最终产生了必须要写一下那“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原初解构主义者的出身牛津的爱尔兰人奥斯卡·王尔德 ”的想法(Saint:viii)。最后,与上述两者密切相关的是政治问题。伊格尔顿指出:“如果说王尔德通常不被认为是生活在英国的爱尔兰人,同样他也不被特别看做一个政治人物。可是,王尔德在政治一词的一切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是政治的。”(Saint:ix)王尔德是激进政治的,并不仅在于他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也不仅在于他为爱尔兰人说话,而且在于他以非常幽默的方式高调调侃了维多利亚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于他从不严肃地对待一切,而只在意形式、外表和愉悦,并非常严肃地进行自我涂鸦。这样,“在维多利亚社会,他无需勾引昆斯伯里侯爵的儿子上床,就会成为国家的敌人”(Saint:x)。这几个方面,在戏剧《圣奥斯卡》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圣奥斯卡》演出剧照(1989年)
《圣奥斯卡》由两幕四场构成,第一幕发生在伦敦,时间在王尔德风化案开庭之前,王尔德先后接待了来访的母亲、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王尔德夫人和作为工运人士和社会主义者的朋友华莱士,他们分别就爱尔兰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第二幕第一场是法庭聆讯,王尔德与昔日三一学院同窗、检察官卡尔逊围绕着道德和义务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场发生在监狱中,同性恋情人道格拉斯前来探望王尔德,最后不欢而散;最后一场是在法国巴黎,潦倒的王尔德与已经变成资本家的华莱士邂逅于咖啡馆,两人再次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由此可见,伊格尔顿既无意于王尔德的文学生涯,也无意于王尔德的生活经历,而试图探讨一个在性、社会和族裔身份上含混不清的社会名流(socialite)和一个社会主义者(socialist)身上所呈现出的极为复杂的现象,同时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历史、文化、政治和文学等问题的理论思考。
全剧始于合唱队的一支“奥斯卡·王尔德谣曲”,它以王尔德式的语言嘲讽地讲述了王尔德的家庭、生活和社会背景。随着合唱队退场,舞台灯光转暗,黑暗中传来一个新生儿的啼哭,从中响起王尔德的声音:“一个恶魔的出生。当他们把我拽出时发出一阵尖叫,并想当场把我杀死:雌雄两个生殖器长在一起。”(Saint:6)灯光亮起时,王尔德已经站在舞台中央,衣着华丽,浓妆艳抹,肥胖光洁,露齿而笑。在随后的第一段独白中,王尔德先对自己的名字发了一通议论:“他们叫我恩内斯特[Ernest,此词与honest(诚实)谐音],恩内斯特·王尔德!这可跟我毫不搭界。一个人花了一生时间与他的名字相左,又怎么会不有点古怪呢?不,这也不对;他们叫我奥斯卡。奥斯卡·芬格尔·奥弗莱尼蒂·威尔斯·王尔德。别人有名字,我有一个句子[sentence,此词还有判刑之意]。我生来就被置于一个判决(sentence)之下。”(Saint:7)的确,王尔德的名字有点古怪,似乎预示着其所有的歧义,其中也包括他的族裔。伊格尔顿曾在别的著述中指出:“王尔德出生在维多利亚中期都柏林的一个英国爱尔兰家庭,而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其姓名中即可看出。他在受洗时被命名为奥斯卡,那是一个传说中的爱尔兰英雄的名字,但王尔德显然不是一个盖尔人的姓。”[5] 接着,王尔德又调侃了自己的身材,称“你们可能会对我何以如此令人生厌的肥胖感到奇怪,那主要是对于爱尔兰民族所受饥饿的补偿。这就是说,我是作为代表替爱尔兰人大吃”(Saint:7)。总之,从一开始,王尔德就与爱尔兰纠缠在一起,而《圣奥斯卡》的第一幕首先就在王尔德母子之间围绕着爱尔兰问题展开。

王尔德母子
王尔德与母亲之间的辩论最清楚地展现了其矛盾性,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王尔德夫人这一镜像最清晰地呈现出了王尔德的矛盾性。在这一场中,身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王尔德夫人试图说服王尔德加入自己的事业,却遭到了王尔德的拒绝。当王尔德夫人急切地要告知爱尔兰的现状时,王尔德的回应是:“请不要给我任何事实,妈妈,它们必定都是想象。”(Saint:10)在讲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芬尼亚组织成员(Fenians)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Parnell)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后,王尔德夫人兴奋地告诉儿子:“如今,我们正在用新武器进行战斗:诗歌、戏剧和音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剧院,我们重新开始使用爱尔兰语写作……奥斯卡,你可以参与其中,而不是把它们都留给年迈的神秘主义者叶芝。”王尔德冷淡答道:“妈妈,你和我都不会讲一句爱尔兰话;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我应该成为凯尔特复兴的先锋。或许,他们该给我配个翻译吧。”(Saint:11)王尔德夫人指责儿子为英国教育所败坏而忘掉了自己的根时,王尔德反驳道:“不是这么回事。当邪恶的英国人讥讽爱尔兰人时,我总是为爱尔兰仗义执言。”(Saint:11)的确,王尔德常常讥讽英国人,但也从不放过讥讽爱尔兰人的机会。因为,王尔德清楚地意识到,作为新教背景的名门望族之后,他与那些爱尔兰农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他和母亲都已不再是爱尔兰人了。对此,王尔德夫人不以为然。她坚持认为,作为名门望族正应当承担起政治领导责任,而王尔德应该像她一样,用自己的口和笔、机智和艺术为爱尔兰人民服务。王尔德的回答则是:“艺术家没有人民。……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当被问及在什么的里面和外面时,王尔德说:“我不知道;这个或那个吧。……我在族裔上是混杂的,在性上可能也是如此。”(Saint:12)更重要的是,“如果我是混杂的,恐怕那也是因为母亲你。你一边满口谈着爱尔兰农民,一边在都柏林开着最时髦的文学沙龙”,而且,“不是你教我模仿英国人吗?不是你在我失去爱尔兰口音后一阵窃喜吗?……不是你把我送到那可憎的灰色寄宿学校,并在我进入牛津大学后大宴宾客吗?”(Saint:12)随后,两人又在如何看待爱尔兰神话、文学和历史等问题上逐一交锋。最后的话题是即将到来的风化案审判,王尔德夫人希望儿子能够像自己当年在青年爱尔兰党创建人达菲(Charles Duffy)审判[6] 中一样慷慨陈词,王尔德还是拒绝了母亲最后的努力——将他变成一个凯尔特人的英雄。谈话不欢而散,王尔德夫人哀叹道:“爱尔兰失去了一位诗人,我失去了一个儿子。”王尔德回答:“简直是废话。爱尔兰人经常失去他们的诗人,就像经常失去他们的贞操一样。你失去的是一个幻想,而不是一个孩子。”(Saint:17)

反映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的讽刺漫画
王尔德夫人失望离去,但争论并没有结束。随后进场的是缠着绑带的华莱士,社会主义者和好斗的工运人士。情绪高昂的华莱士告诉王尔德,前一天刚刚爆发了工人示威(他的手臂就是在与警察厮打时受伤),而近来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王尔德打断他,“我们不能谈点重要的事吗?比如,波德莱尔”。华莱士没有理会,继续滔滔不绝。他告诉王尔德:“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组成了新的联盟。莫里斯(William Morris)将是新的领袖。……这一切都和你有关,奥斯卡。你的事业和工人们的斗争是一致的。”(Saint:22)王尔德表示:“我没有任何事业。……我唯一的斗争就是在不拉伤自己的情况下起床,那不关无产阶级的事。”华莱士说他想到的是就要开庭的诉讼,王尔德说“那只能和上床有关”(Saint:22)。随后,华莱士发表了长篇宏论,试图证明在王尔德和工人之间确实有着关联。大意是,统治阶级之所以抓住王尔德的性生活不放,就是因为王尔德破坏了性-财产市场。要是贵族和有产者的儿子们都变得性反常,谁来迎娶那些初入社交界的淑女们呢?又有谁来继承他们的财产呢?所以,王尔德做的事情和工人们的斗争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只是,王尔德自贵族和有产者那里夺走的是子嗣,而工人们夺走的是钱袋。对此,王尔德重复了他早先对母亲说的话:简直是废话。当华莱士质疑王尔德是否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时,王尔德断然答道:“我当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你没看到我为孩子们写的那些童话故事吗?它们都是革命的牵引车。”(Saint:23)平心而论,在王尔德的创作中,那几篇童话作品的确引人向善,因而深受儿童和成年人的喜爱。在谈到无政府主义、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王尔德终于讲出了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真意,那就是“无所事事”。在剧中,王尔德这样谈论他的“无所事事”:“以对自我的神圣献身,我预示着新的耶路撒冷,于其中所有人都可以全然成为他们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在骨子里就无所事事:以见证一个人人都无需工作的时代。……但是我的无所事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必须要极为艰苦地成就它。你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未来的象征不是那么容易。”(Saint:24)这里的台词当然出自伊格尔顿之手,但王尔德也确实表达过这样的思想,这仅从他那两篇重要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论无所事事之重要》(“The Critic as Artist:With Some Remarks Upon the Importance of Doing Nothing”)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伊格尔顿曾对这两篇文章做过深入的分析,并给予王尔德的社会主义思想极高评价。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1891年版)
在伊格尔顿看来,王尔德的社会主义是要以自动化取消劳动,以使所有人都能够自由地塑造自己。这是一种带有明显王尔德个性的反转: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在于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而他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保证他的个人主义,并最终使其为所有人所拥有。在这一点上,王尔德与更为正统的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从不诉求取消劳动,而只是想依据中世纪手工作坊的模式将劳动转化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因此,“虽然莫里斯是社会主义者而王尔德不是,但就此而言,王尔德更接近马克思的看法”(“Introduction”:xxii)。固然,王尔德完全不了解社会关系,也就不知道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以所有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这不仅使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变得极为不切实际,而且也损害了其原本具有深刻内容的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经典,时至今日仍然是一份吸引人的基本文献”(“Introduction”:xxiii)。
在通常认为应该是戏剧高潮的审判一场中,伊格尔顿和他笔下的王尔德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语言风格。在与王尔德夫人的谈话中,当被问及他将如何为自己辩护时,王尔德表示,他要“运用那屡试不爽的法律手段;其以谎言为人所知”(Saint:17)。同时,他也拒绝了母亲要求他在法庭上强调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冲突的策略,声称“我将以我的方式回答那些指控,运用机智和狡黠”(Saint:17)。这两点他都做到了,也都没有做到,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检察官卡尔逊要求王尔德告诉法庭他如何打发时间时,王尔德答道:“大部分时间是无害的。模仿英国上流社会。着装。我要花很多时间着装。然后是卸装。这其间留下的时间不多,无暇任何不法行为。”(Saint:34)在被质询他与那些年轻男子交往的目的何在时,王尔德答道:“我关心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问题。我认为一位绅士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自己的教养是他的责任。我的目的是教学(pedagogy),而不是鸡奸(pederasty)。”(Saint:36)经过几位证人作证和一番当庭辩论后,卡尔逊宣称:“王尔德先生,我指控你游手好闲、性欲倒错、放荡淫邪、腐化堕落。”王尔德的回应是:“我拒绝指控,但欣赏控词的头韵。我假定你想表明我是一个艺术家,可没有必要在指控中使用这样的委婉语。较之在英国,在我们那里艺术家更受尊重,我们把他们驱除出去。”(Saint:41)这里的“那里”既指爱尔兰,同时也暗指柏拉图的城邦。事实上,在当时的审判中,王尔德真的以追求柏拉图式的爱情作为自辩的理由之一。卡尔逊穷追不舍,语带讥讽地问王尔德是不是觉得在英国自己像个外国人?王尔德反唇相讥:“没错,可我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你们足够好心去教我说话。但就像卡列班一样,我学会的是如何诅咒。”(Saint:41)这马上让人想起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那本《学会诅咒》(Learning to Curse:Essays in Early Modern Culture)。在最后的申辩中,王尔德的确用优雅的英语诅咒了维多利亚英国的虚伪、傲慢和强权。在《异端人物》中,伊格尔顿谈及王尔德的机智语言的犀利与幽默时曾表示,那些所谓的不合逻辑、荒唐可笑(Irish bulls)“可以被视为殖民地人向帝国主义父语(father-tongue)复仇的最好例证。……他[王尔德]的爱尔兰式幽默是典型的反常的和揭露性的,是对于高高在上的英语之寡淡热心的一种属下抗议”[7]。较之于王尔德在性倾向上的反常,这种语言的反常更使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社会感到不安和难以容忍。

1895年5月4日The Illustrated Police News的头版头条:
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案
王尔德与华莱士的再度相见是《圣奥斯卡》中最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之一。此时,王尔德已经流亡异国,穷困潦倒,不名一文,孤身一人,再无酬酢。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华莱士惊喜地发现了呆坐在咖啡桌旁的王尔德。在相互讲述了一些近况后,王尔德问起英国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劳工运动的发展。这时已承继父业而变身为资方人士的华莱士告诉王尔德,工人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已不再有大规模的劳工组织集会了,有的只是慈善赈济活动。而且,人们正在讨论成立一个工党,那可以绝妙地把工人阶级的好斗分子转化为中产阶级的政客。在这个国家转型时期,人们所能抱有的最好希望就是出现一个“更为人道的资本主义”。王尔德对此嗤之以鼻,称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期望的希望。如果有什么值得期望,那应该是一个“所有人都被允许成为他们自己的社会”(Saint:57)。华莱士说,他看到了王尔德的最后变态/反转(perversion):作为一个身败名裂的社会名流,却在异国他乡翘首期盼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英国。谈及希望,王尔德这样说道:

噢,理查德,我抱有希望,许多希望。当然,不是为我自己。但你肯定不会想象一百年以后英国还会禁止同性恋吧?那太荒诞了,这长久的愚蠢总会有个结束吧;我们不是已经不再烧死女巫了吗,是吧?从现在开始的一百年内,每个人都将是雌雄同体,工人将掌管社会,政府将每年向爱尔兰支付百万英镑赔款。如果坎特伯雷大主教还存在,他将是一个穿着网眼长袜、头戴宽檐软帽的锐舞会迷(a raving queen)。没人还会记得大英帝国,工业生产将全部自动化,人们一天到晚四处闲逛,身穿大红斗篷,相互背诵着但丁的诗句。(Saint:57-58)

这就是王尔德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希望,而最后一句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8] 在华莱士表示那不过是梦想后,王尔德仍然坚称,“我能够梦想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是一个有远大未来支撑的人”(Saint:58)。华莱士说他实在看不出王尔德像是一个未来的形象。王尔德答道:“我是一个当下失败的形象。那是唯一值得拥有的未来形象。”(Saint:58)显然,相对于已对未来感到悲观的华莱士来说,王尔德对未来仍然充满了希望,即使那是一种与现实政治和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实际关联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显然是站在王尔德这一边,就如詹姆斯·史密斯指出的:“伊格尔顿在《圣奥斯卡》中自王尔德那里辩证地引出的一种希望表明,王尔德的那种社会主义未来的美学如今仍然具有生命力。”[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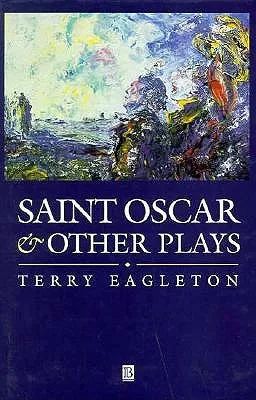
《圣奥斯卡和其他剧作》
在华莱士退场后,法官卡尔逊进场。两人不仅同样来自爱尔兰,而且同是都柏林三一学院的学生。忆起两人彻夜畅谈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往事,正所谓曾几何时,风华正茂,挥斥方遒。令王尔德不解的是,虽然两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最终却水火不容。在谈话中,王尔德对卡尔逊说,“你总是善于着装,……你和我恰好相似,真的;永远是一个戏剧演员”。卡尔逊不完全赞同,称“我说话就像我所是的爱尔兰人,可这对你并不完全适用”。王尔德答道:是啊,“我用英国口音为爱尔兰讲话,你却操着都柏林口音为英国辩护”(Saint:61)。不过,王尔德始终搞不清楚的是,自己为什么会被唾弃,难道“我威胁到了你们的男子气概吗?”对此,卡尔逊明白表示:“我才不在乎你的性生活呢,我承担诉讼是因为必须要使你不再为害。我有实现此目的的最好辩才,唯一能够与你匹敌的辩才。”对于王尔德何为有害的质询,卡尔逊的回答是:“因为你无所归属。因为你没有信仰。”(Saint:61)随后,卡尔逊发表了长篇大论,大谈先辈在英国这片土地上的劳作与汗水以及上帝的恩典与救赎。这不禁让人想起伊格尔顿早年积极参与的天主教左翼活动以及近年来的“神学转向”,其中“反转”(reversal)正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10] 不过,更为有趣的是,在斥责了作为艺术家的王尔德及其文学创作和唯美主义——“机智、艺术和愉悦”——之无益后,卡尔逊却声称,“只有一件艺术品,奥斯卡,那就是未来”(Saint:63)。虽然卡尔逊明确否定了艺术家在构建未来中的作用,但王尔德所推崇的艺术也并非狭义,就如他在第一场中与华莱士谈论社会主义时所言:“最高的艺术形式是成为自己的艺术家。”(Saint:25)这样,两个人的目标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只是达至目标的途径不同而已。
在戏剧结尾的最后一段独白中,不久人世的王尔德谈起了自己的墓志铭:

我想让人们在我的墓碑上写下:“这里长眠着奥斯卡·王尔德,诗人和爱国者。”不,这听上去有点简单,也不那么真实。这么写如何:“这里长眠着两位王尔德:社会名流和鸡奸者,泰晤士和利菲,吉基尔和海德,贵族和底层人。”我可以有两座坟墓和两块墓碑;朋友们可以选择其一哀悼,也可以两个换着凭吊。(Saint:64)


王尔德墓
这就是王尔德对自己的盖棺论定,也是伊格尔顿对王尔德的最后裁定:一个双重性格者,一个矛盾集合体。伊格尔顿在其选编的《王尔德戏剧、诗文集》的引言中对此有更清晰的分析:“王尔德说过,艺术中真实的矛盾方面也是真实的,而这完全可以用来谈论王尔德本人那绚烂而颓败的生涯。……王尔德得到了其出生的城市都柏林(Dublin)的喝彩,那座城市被其同胞和同道詹姆斯·乔伊斯拼写为‘Doublin’;同样,王尔德的一切都是双重的、混杂的和含糊不定的。”(“Introduction”:xi)王尔德的双重性(doubleness)并不难以察觉,困难的是如何理解造成这种双重性的原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了伊格尔顿的敏锐性和深刻性:

作为一个隐秘同性恋者的社会名流,王尔德生活在其公众身份和私人自我的冲突之间;而两者之间的这一裂隙引人注目地成为其时代的典型现象。世纪末(fin de ciècle)为吉基尔和海德、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这样的人物所烦扰,为某种犯罪和无政府力量在体面社会的平静表层之下暗流涌动的感觉所缠绕。如果说这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它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流连于社会底层的时代,就像道连·格雷一样陷入那为上流社会所压制的肮脏和惊悚的“下层社会”[Nether World,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小说的标题]。并非偶然,这也是弗洛伊德开始发现负疚、罪感和狂想的隐秘之所在的时期,其称之为无意识。1880和1890年代是亚文化和地下世界、社会实验和奇异耸动、邪教和怪诞、反常和奇幻开始风行的时代,而性解放、宗教密仪和政治革命的新潮也开始搅动。在这个意义上,世纪末作为一个反抗的享乐主义和乌托邦幻象的时代强烈地预示着1960年代。(“Introduction”:xi-xii)

这就是王尔德生活的时代,也是道连·格雷生活的时代。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伊格尔顿生活的时代。

《道连格雷的画像》插图
这把我们引向了最为有趣的一个问题:在伊格尔顿的《圣奥斯卡》与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理论家和批评家们的注意。例如,阿德逊的《特里·伊格尔顿》一书的第四章就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其题为“一幅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A Picture of Oscar Wilde?)。伊格尔顿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圣奥斯卡》中至少有两次提到了《道连·格雷的画像》。第一次是在第一幕结束时,合唱队在一支哀叹王尔德命运的谣曲中唱道:“你从未遇到一位天才如此活力四射和胆大妄为,但在沉寂阁楼中他的画像正在老去。”(Saint:30)第二次是在第二幕中间换场时,由狱中囚犯组成的合唱队唱道:“道连已变成了他的画像”(Saint:48)。如果说《圣奥斯卡》是王尔德的一幅画像,它和《道连格雷的画像》之间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是,不同于后者中画像变得老迈丑陋,生活中的道连却永葆青春美艳,王尔德在生活中不断衰颓,在画像中却韶华依旧。在伊格尔顿为《王尔德戏剧、诗文集》撰写的引言中,他也多次谈及《道连·格雷的画像》与王尔德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在伊格尔顿看来,于《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一些焦虑和不安的因素,它们构成了一种负疚、自我背叛和信义尽失的感受(“Introduction”:xiv)。而且,“他[王尔德]未来之毁灭的阴影已经预言式的笼罩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之上,在其异常光鲜的外表之后,那可怕的秘密已经在酝酿成形。王尔德把自己笨拙、健壮的身体装扮于奇装异服之中,但在这些诱人的外表之下,他的灵魂如同道连的肖像一样,与传统道德价值渐行渐远”(“Introduction”:xv)。其实,发现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的自传性质并不困难。王尔德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明确表示:“贝泽尔·霍尔渥德是我认为的我个人的写照;亨利勋爵在外界看来就是我;道连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11]。更重要的是,就如同许多人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看到了王尔德的影子一样,我们在《圣奥斯卡》中也可以找到伊格尔顿的身影。或许,还是王尔德说的对:“凡是怀着感情画的像,每一幅都是作者的肖像。”[12] 而且,如同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几个不同人物身上皆有王尔德的这一面或那一面的写照一样,在《圣奥斯卡》中的主要人物身上,也都体现出伊格尔顿的不同侧面。如果套用王尔德的句式,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圣奥斯卡》中,卡尔逊是伊格尔顿认为的他个人的写照;华莱士在外界看来就是伊格尔顿;王尔德是伊格尔顿愿意成为的那类人——可能在别的时代。在其自传体著作《守门员》(The Gatekeeper)中,伊格尔顿曾谈到自己与王尔德的某些相似之处:

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我发现自己在著述中如此经常地谈及这位英国-爱尔兰的出身牛津的原初-后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作为英国显贵和爱尔兰乡巴佬(patrician and Paddy)的奇特混合,他那凯尔特式的轻佻与严肃之结合。他以由来已久的爱尔兰方式逃离一片死气沉沉的殖民地后,只能四处兜售其语言的机智,就像我和其他许多一无所有的人一样,只能凭借语言资本脱离工人阶级家庭。[1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王尔德-伊格尔顿式的辩证反转。凭借语言的机智,王尔德逃离了殖民状态,伊格尔顿脱离了劳工阶层,但最后的结果却是,王尔德从上流社会堕入社会底层,而伊格尔顿却由工人子弟变为学术大师。

特里·伊格尔顿
《圣奥斯卡》明显属于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其主要包括理论三部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Studies in Irish Culture,1995)、《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1998)和《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抗者》(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 Century Ireland,1999),以及三部戏剧《圣奥斯卡》(Saint Oscar,1989)、《白色、金色和坏疽》(The White,the Gold,and the Gangrene,i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1997)和《上帝的蝗虫》(God’s Locusts,i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1997)。伊格尔顿对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关注和投入,既得到了赞扬也招致了批评,如史密斯指出的:“这里存在着某种风险,伊格尔顿的‘爱尔兰’书写可能被看作其真正‘专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怪异‘副业’;或者,在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和其关于民族主义及其论争的书写之间,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且,这后一点的确已经为伊格尔顿招来了不断的指责。”[14] 不过,本文的兴趣不在于此(此问题将另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中,既有理论著述,也有文学创作。而且,后者明显早于前者。这就是说,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始于文学创作。也许,这里并不存在有意为之的出版顺序。但无论如何,这证明了本文在开篇就指出的伊格尔顿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倾向:将理论与创作、思辨和想象融合为一,而这正是伊格尔顿从王尔德那里学到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圣奥斯卡》这一“思想剧”才在伊格尔顿的著述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1] See Stephen Regan,“Preface”,in Stephen Regan,ed.,The Eagleton Read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Ltd.,1998,p. xiv.
[2] See Terry Eagleton,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Ltd.,1997,p.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格尔顿还谈及了何以他会选择戏剧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形式:在所有文学形式中,戏剧具有最强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与行动密切相关,因而是最具政治性的文学活动。
[3] David Alderson,Terry Eaglet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 144.
[4]Terry Eagleton,Saint Oscar,New Jersey:Field Day,1989,p. vii.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 Terry Eagleton,“Introduction”,in Terry Eagleton,ed.,Oscar Wilde:Plays,Prose Writings and Poems,London:David Campbell Publisher,Ltd.,1991,p.xii.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6] 伊格尔顿曾经将达菲审判和王尔德审判联系在一起,而达菲当时的确也被指控有伤风化(see Terry Eagleton,Figures of Dissent:Critical Essays on Fish,Spivak,Žižek and Others, London:Verso,2003,p. 50)。
[7] Terry Eagleton,Figures of Dissent:Critical Essays on Fish,Spivak,Žižek and Others,p.49.
[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5页。
[9] James Smith,Terry Eaglet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p. 136.
[10] 关于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参见拙文《奇迹与革命性反转:特里·伊格尔顿的神学转向》,载《汉语基督教学术评论》第14期,台湾中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11-130页。
[11] 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上),苏福忠、高兴等译,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06页。
[12] 奥斯卡·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荣如德译,载《王尔德全集·小说童话卷》,第9页。
[13] Terry Eagleton,The Gatekeeper:A Memoir,London:Penguin Books Ltd.,2001,p. 161.
[14] James Smith,Terry Eaglet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p. 118.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