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中的“思想之战”
编者按
我们不应孤立地讨论奥斯丁小说《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达什伍德和她妹妹玛丽安的思想差异,而要充分注意两位女主人公和约翰·达什伍德之间的对立。后一分歧从属于一场由来已久的文化讨论,即在逐渐生成的敛财逐利社会(acquisitive society)里,由艾狄生、斯蒂尔、笛福及理查逊等作家就人的精神需求、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等等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究。本文试图把埃丽诺和玛丽安之间的对照和对话更多地放到上述背景里考察,将两姐妹在多重社会语境中的人生波折和对应选择看作构思某种局部抵制敛财逐利社会的私人乌托邦的尝试。
作者简介
黄梅,女,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简·奥斯丁像
简·奥斯丁(1775-1816)说,她写作有如在一小片象牙上工笔绘画,所涉不过乡村中三四户人家的一小段生活。[1] 然而她的小说自1811年问世以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影响持续而深远。为什么呢?
早期西方评论大都把奥斯丁的名气归结于她的艺术造诣和她对人性的洞察。不过,自二十世纪中期“新批评”渐渐式微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密不可分,意识到奥斯丁小说对当时社会生活和思想建设的深刻介入,从而把对她的重视和理解都提到了新的高度。如威廉斯所说:并非只有惊天动地的拿破仑战争才算大事,历史有许多暗流,当时英格兰地产主家庭生活的社会史(也即奥斯丁的题材)就是最重要的事态之一。[2]
本文标题中“思想之战”的说法来自英国著名学者玛丽琳·巴特勒的《简·奥斯丁和思想之战》(1975)。巴特勒和达克沃斯[3]等是最早关注奥斯丁小说主题思想的评家,他们都强调奥斯丁的保守倾向。巴特勒认为:在奥斯丁开始写作的1790年代里,由于法国革命造成巨大冲击,英国思想文化界存在激烈的论战。论争的一方为张扬情感主义、信赖个人追求、推崇“自然”的激进派(雅各宾派),另一方是重视理性、责任和自我节制、强调群体关系、讲求“人工”或“艺术”的保守派(反雅各宾派);而奥斯丁深受后者影响。《理智与情感》一书是“反雅各宾寓言”的一个鲜明代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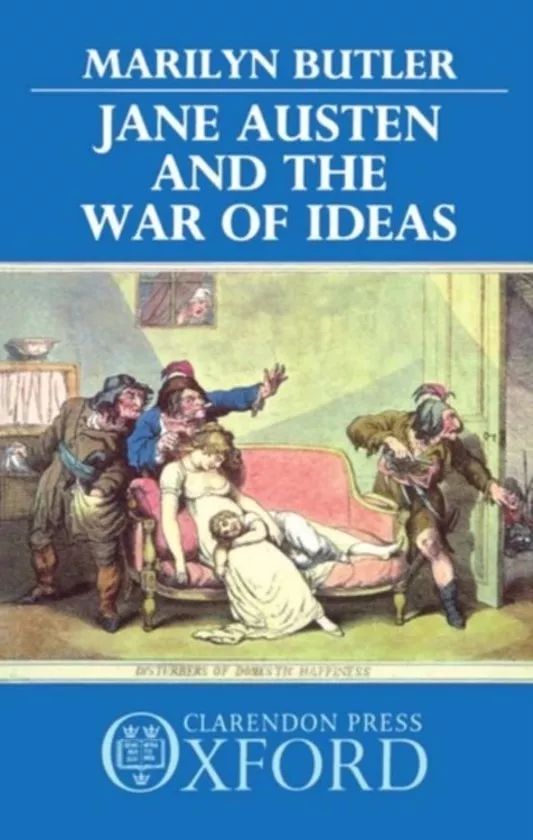
玛丽琳·巴特勒的《简·奥斯丁和思想之战》
确实,“理智”和“感情”等等两百多年来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关键词。[5]《理智与情感》一书从本质上说不是在演绎浪漫的爱情史,而是在展示并展开思想论争。[6] 不过,巴特勒一派的学者过分注意它与简·韦斯特(Jane West,1758—1852)的《饶舌者的故事》(1797)等“两姊妹小说”的相似之处,孤立地剖析埃丽诺·达什伍德和她妹妹玛丽安所分别代表的“理智”和“情感”的对立,从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两位女主人公所共同分享的大生存环境,忽略了小说中最重要的论争营垒首先在两位女主人公和约翰·达什伍德之间划分。与此相关,过多地着眼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激进”和“保守”之争,也使一些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另一个涉及面更广、延续时间更长的重大文化讨论,即在一个正在生成的敛财逐利社会(即R.H.Tawney所说的acquisitive society)里,艾狄生、斯蒂尔、笛福及理查逊等一脉相承就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规范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究。[7]
如果我们把埃丽诺和玛丽安的对照和对话更多地放到上述背景里考察,就不会简单地用“激进”、“保守”之类词汇来界定奥斯丁传达的信息。本文试图把达什伍德家两姐妹在多重社会语境中的人生波折和对应选择看作构思某种局部抵制“敛财逐利社会”的私人乌托邦的尝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巴特勒的观点有所拒斥,对与她唱反调的一些论者也不尽认同。因为后一类评论大抵像巴特勒一样聚焦于个人与群体的冲突,只不过更侧重揭示奥斯丁作品中个人意志对社会制约的反抗,以“颠覆性”取代“保守”说。[8] 两方的观点其实都更多地反映了“我们时代无视个人与群体生活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思想偏向”[9],而在奥斯丁笔下,对两者关系的展示和探查是多方位的,紧张和对立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约翰·达什伍德的世界
《理智与情感》和《饶舌者的故事》写于同一时期,且都对比描述两姐妹不同的人生态度和婚恋历程。不过,奥斯丁的小说与后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其中的背景人物相对广泛丰富,并被放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上。
《理智与情感》以极富象征意味的“父之死”开场,首先讲述了两桩丧事和由此而来的两次遗产继承。先是老乡绅达什伍德去世,他的侄儿亨利 达什伍德继承了诺兰庄园。不到一年,亨利本人也撒手归西。按照老达什伍德的遗嘱,庄园及其附属地产必须传给男性子嗣即亨利前妻所生的儿子约翰及约翰的儿子哈里,因此亨利的续弦达什伍德太太和她的三个女儿(埃丽诺、玛丽安和玛格丽特)能得的财产“微乎其微”。
亨利临终前要求约翰照料继母和妹妹,后者迫于常情不得不应允。约翰为人精明,办事得体,是受世人尊敬的有产者。他经过权衡,打算送三个妹妹每人一千英镑,并且很为自己的慷慨自得。但是他的妻子范妮强烈反对,她认为同父异母兄妹算不上亲属,不应该把钱无端地送给异母妹妹,把自家的独生子“刮成穷光蛋”(第2章)。[10] 约翰立刻被范妮的逻辑征服了。他说,把钱数减半,也管够她们发财了。再一合计,几个女孩本来也不差钱,简直不需要什么补贴。于是约翰又说,不若一年总共给继母一家一百镑年金。范妮答道,这固然比一下出手一千五要好,“不过,要是达什伍德太太活上十五年,我们岂不是上了大当?”她举例子说当年她父亲立遗嘱规定给三名老仆支付养老年金,结果一年年下来,想甩都甩不掉,眼看钱被刮走了,自己却做不得主。约翰醒悟过来:其实偶尔给几个小钱,送上三五十镑,比年金强多了——“因为钱多了,她们只会大手大脚”。范妮说:

我认为你父亲根本没有让你资助她们的意思。我敢说,他所谓的帮助,不过是让你合情合理地帮点忙,比如替她们找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啦,帮她们搬搬东西啦,等季节到了给她们送点新鲜野味啦,等等。我敢以性命担保,他没有别的意思……想一想,你继母和她的女儿靠着七千镑得来的利息,会过上多么舒适的日子啊。况且每个女儿还有一千镑,……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那么四个女人家……她们一无车,二无马,也不用雇仆人。她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舒服!一年五百镑哪!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怎么能花掉一半。……论财力,她们给你点倒还差不多。

她还更进一步对继母分得了家用器皿和台布之类物品愤恨不已:“你父亲光想着她们。我实对你说吧,你并不欠你父亲的情,也不必理睬他的遗愿。”夫妻俩最后断定,约翰对父亲的承诺,落实到待继母搬家时“邻居式”地帮帮忙就尽够了,再多不但“绝无必要”,而且“非常不合体统”(第2章)。
在这段戏剧性对话中,范妮一方面贬损、排斥约翰和父亲及异母妹妹之间的关系、感情和责任;另一方面用感情色彩非常强烈的词语把资助妹妹之举说成毁掉儿子一生的灾难,最终成功地把拟议中的资助额度从一千镑降至为零。伊安·瓦特说,这是奥斯丁最有力量、最精彩夺目的讽刺文字。[11] 要充分体味其中的挖苦,我们得对当年英国绅士们居家度日的“政治经济学”有所了解。当时各档次“绅士”家庭年收入大约从一百镑到四千镑。前者是下限,刚刚够在温饱之余雇个把佣人干粗活儿并加盟流通图书馆借书看。两者之间,几乎每百镑一个档次,收入可以相当精确地通过住房、仆人、家具、马匹和车辆等消费标志体现出来。年收入高于四千镑的人家就超出普通绅士范围了。他们将名副其实地位列“上等社会”,可以毫无顾虑地花钱,还可以在伦敦城里另置办一处住宅供社交季节使用,等等。[12]
具体到亨利的继室达太太,丈夫死后她收入骤减,还有三个待嫁女儿,已落到士绅群体的底层。而约翰呢,他得了母亲的财产,结婚时又从女方捞了一大笔钱,叔祖父老达什伍德传下来的诺兰庄园还可给他每年另添四千镑收入。可见此时他已是巨富,其“价值”直追《傲慢与偏见》中令人垂涎的单身男性达西(年收入一万镑)。与其财产相比,他打算资助妹妹们的三千英镑可以说丝毫不伤筋动骨。为这小小馈赠,约翰迫于老父临死恳求才动念,而后又沾沾自喜,说明他何等小气。正因如此,范妮的言辞在他听来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约翰还另有一场出色的表演。兄妹再次相逢是在伦敦。那时达氏母女早已搬家租住远亲约翰·米德尔顿爵士的一处乡舍。埃丽诺和玛丽安随约翰爵士的丈母娘詹宁斯太太到伦敦小住。
约翰到伦敦两天后出门为妻子订制图章,在一家珠宝店与妹妹们不期而遇。他首先表示早想去看望她们,实在抽不出时间;又说听人议论米德尔顿夫人和詹太太都很有钱,而且处处照应继母一家——“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们都是有钱人,和你们又沾亲带故,按理是该对你们客客气气,提供各种方便,让你们能过得舒舒服服”。一番话直说得埃丽诺在一旁为他羞愧不已。小说中“羞愧”一句是炉火纯青的奥斯丁式妙笔。约翰自私得那么堂而皇之、刀枪不入,那么完完全全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之中,似乎全然忘记了他比米德尔顿或詹宁斯们更“沾亲带故”,几乎也可以断定也更有钱,忘记了他们夫妇把继母和妹妹从老宅扫地出门连一个指头的忙都没有帮。这种种事实都不再点明,只是暗藏在听者兼受害者埃丽诺的“羞愧”中,让读者自去体味徐徐地渗出的层层挖苦。
翌日约翰到詹太太家拜访,和埃丽诺说起自己的丈母娘费拉斯太太正在力促长子爱德华娶个阔媳妇。扯出妻舅爱德华不是信口闲聊,而是因为他和范妮及费太太都看出埃丽诺与爱德华的关系不一般,这样放话为的是让埃丽诺彻底断念。不过,提起费太太,约翰便情不自禁地赞美起她老人家“高尚的精神”来,原因是他们一进城老太太就塞给了范妮两百镑钞票——“真是求之不得呀”:

“我倒不是叹穷叫苦,我们的收入无疑是相当不错的,我希望有朝一日会更上一层楼。不过,正在进行的诺兰公地的圈地耗资巨大。另外,我这半年里还置了点地产——东金汉农场,你一定记得那地方,老吉布森以前住在那里。那地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我都十分理想,紧挨着我家的地产,因此我觉得有义务把它买下来。假如让它落到别人手里,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责备。人要为自己的便利付出代价,我已经花费了一笔巨款。”
“你是不是认为那地其实值不了这么多钱?”
“哦,我想那倒不至于。我买后第二天本可以再卖掉的,还能赚钱。不过说到付款,我当初倒真有可能会遭逢不幸呢,因为那时股票的价格很低,我若不是碰巧有足够的现钱存在银行,就得大蚀其本地卖股票了。”(第33章)

听听!他正在圈占村庄公地,在购买吞并邻家的地产,而且染指金融投资和投机(买卖股票)。可见约翰绝非一般的抠门乡村绅士,他是雄心勃勃的农业资本家。在奥斯丁写作的年代里,英国传统农村社会正处在解体前的最后挣扎阶段[13],大规模圈地是农村资本主义化的关键“动作”之一。[14] 威廉斯说:当时英国社会处于活跃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划一而固定”,其时“敛财逐利的正宗资本社团与农业资本主义的瓜葛最为明显”。[15] 出身地主世家的约翰·达什伍德作为农村资本的精明代表,正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
范妮和她的母亲费太太与约翰构成了巩固的利益和思想同盟。若说有区别,只是那母女俩自私得更冷酷、更粗俗,有时也更糊涂任性一些。她们希望自家长男爱德华“出人头地”(第3章),处心积虑撮合他和贵族阔小姐莫顿的婚事。后来,爱德华因和穷姑娘私下订婚被母亲剥夺继承权,有位布兰登上校出于同情给他提供了一份年俸两百镑的牧师职务。约翰闻说此事,大发感慨:

哦,握有那样收入的职位,若是在已故牧师病重、位置马上要出现空缺时处理,他本可以到手一千四百镑的。……现在嘛,委实有点太晚了,再推销也不好办了,可是布兰登上校是个聪明人呀!……他竟然这么没有远见!(第41章)

他的反应恐怕出乎多数人的意料。他不推敲布兰登的动机,不探究其道德取向,也不为爱德华(毕竟也是近亲)感到庆幸,甚至忘了站到费太太立场上谴责爱德华,而是直奔牧师职位背后的金钱交易。当时,一地最重要的地主士绅常有权决定出任本堂区牧师的人选。约翰的头脑立刻换算出这一权力值多少现金。想到布兰登没有未雨绸缪、及早挂单沽售即将出空的神职,将一个赚钱机会白白放空,他不禁扼腕痛惜此事不直接涉及他本人和小家庭的利益,而是事关思想的“正道”。这类本能反应不但充分揭示了约翰们的思维方式,也说明十九世纪初英国社会生活已经市场化到何种地步。
约翰是奥斯丁笔下少有的鲜明生动的农业资本家形象,一言一语活灵活现,给读者带来无穷乐趣,几乎让人想猜测他的原型究竟是奥斯丁近旁的哪一位。正因为约翰不像他妻子和丈母娘那么狭隘恶毒,就更反映和代表了金钱逻辑的“理性”,在更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资本的人格化。他把财产的增长当作自己的“义务”和“良心”,“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16],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表达特定话语体系的“说话人”(speaking person)。[17] 他理直气壮地图谋私利,毫不掩饰地向一切有钱人致敬,但很少生出不利己的损人之心。如叙述者说:“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第1章)反讽的芒刺穿透过平静的语句,指向个人行为之外的世道。
另一个对于小说情节发展及思想表达至关重要的背景人物是露西·斯蒂尔小姐。露西是故事讲到一半才中途(第21章)登场的。她和姐姐南茜是詹宁斯太太的亲戚,喜欢热闹的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和詹太太便请她们来做客。露西听到约翰爵士拿玛丽安和埃丽诺的心上人开玩笑的闲话。不久后她便开始向埃丽诺倾诉心曲。她问埃丽诺是否了解费拉斯太太的性格,然后吞吞吐吐地解释道,自己唐突发问是因为她和爱德华·费拉斯订婚已有四年。她说,爱德华曾在她舅舅家读书,他们因此相识相爱以至私订终身,只因她太穷不可能得到费太太认可,两人不敢公开婚约。她搬出爱德华的亲笔信件(按当时习俗,只有订婚的男女才通信)等给埃丽诺看,称埃丽诺是自己最信赖的朋友并恳请她保密。
露西订婚一事被南茜不小心捅出去以后引起轩然大波。爱德华通告露西自己将陷入贫困,把选择权交给了她。露西信誓旦旦要和他共度艰危。她写信给埃丽诺,说困境深化了她和爱德华心心相印的幸福,求埃丽诺帮爱德华在教会谋个职。她谦卑的求助信确实生了效。不过此后事态发展却令众人目瞪口呆。不显山不露水她完成了战略大转移。没过多久露西致信爱德华,宣布说“鉴于我肯定早已失去了你的爱情,我认为自己有权利去爱另外一个人”,还说自己爱上了爱德华的弟弟,“我们两人彼此离开了就活不下去……“(第49章)。爱德华鄙薄她的文笔。不过,就其想达到的目的看,露西的信是无懈可击的——把毁约的责任全推给了爱德华,还很周到地提醒他应保持惯有的“宽怀大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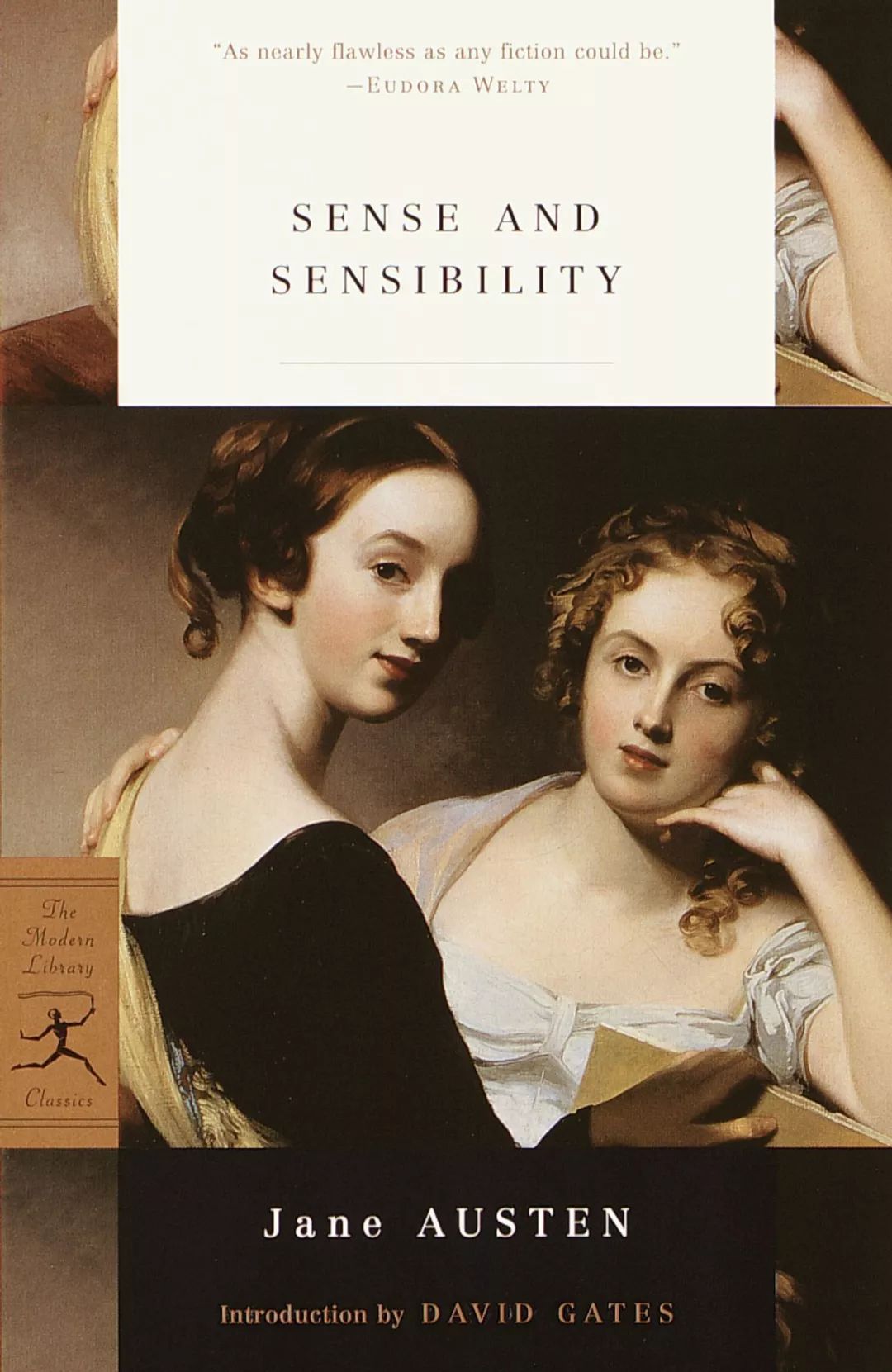
《理智与情感》
露西·斯蒂尔是小说中出身最微贱的人物之一。叙述没有细致交代她家境况,只说她比埃丽诺社会地位更低,很可能也更穷。斯蒂尔姐妹总是寄住在各种亲戚朋友家,转战于社交界边缘,伺机步入婚姻市场。她们受的教育极为有限,平素连零用钱都缺少,我们甚至不清楚在衣料十分昂贵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她们靠什么维持体面甚至时髦的衣装(凭露西的十分了得的女红功夫!)。而要挣到在各家白吃白住白玩的出入证,又谈何容易?达氏姐妹的遭遇已经表明,在那个世道里亲戚关系是可讲可不讲的。斯家姐俩所能依靠的唯有露西一张战无不胜的甜嘴巴,还有她的谦恭和勤劳。米夫人只需提提女儿对某件礼物的期待,露西就会立刻放弃打牌坐到烛台下去编织,还一脸的喜幸,仿佛这是天底下最让她高兴的事儿。不是每个人,甚至不是每个地位卑微的穷人都能当这么好、这么有用的陪客的。她能让约翰·达什伍德夫妇撇下自己的妹妹而邀请她们来家小住,是她能力的证明。
露西和埃丽诺打交道也进退有序。她从邻居闲谈得知埃丽诺是危险的情敌,这与她对爱德华的观察相吻合,于是她自曝订婚秘闻,让埃丽诺及早出局。她对埃丽诺之类的淑女吃得很准。她诉诸埃丽诺的荣誉感和良心,反复恳谈,不让后者对爱德华的情意有任何反弹的机会,也从不放过不露声色地伤害后者的机会。露西对付费拉斯兄弟的手段更是高明无比。她先是以忠贞爱情的名义断然拒绝在爱德华失宠时解除婚约,很显然,即使失去继承权的爱德华也聊胜于无。后来,因哥哥倒霉而得了大笔家产的纨绔哥儿罗伯特自告奋勇来劝她退婚,她把握时机小心迎合,让罗伯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成功。结果一次次恳谈下来,罗伯特满意地发现自己的魅力远远超过哥哥。于是露西摇身变为罗伯特·费拉斯太太,充分展示了她出神入化的看人下菜碟的功夫,也典型地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中“婚姻的缔结……完全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18]的情状。最终这位高明的婚事谋略家成功地推销了自己,让我们深信若有机会她定能经营更大规模的商务。
露西是奥斯丁笔下最高明而稳妥的成功“野心家”(若不计少年习作中的苏珊夫人)。如果说约翰·达什伍德和费拉斯母女体现了立在明处的有产者的唯利是图,那么露西则代表了尚藏在暗处的“谋产者”的精明和狡黠。[19] 而且,与约翰开口资产闭口价格的情况相反,露西满嘴情意,几乎不提钱字,谋求财富的目的深藏在符合通行道德观念的语言和行动之下。
小说中还有其他一些背景人物具有比较纷杂的过渡色彩。他们在思想上与约翰·达什伍德有根本的相似之处,但不那么心无旁骛地逐利。关键男性人物威洛比是其中之一。他先是以浪漫恋人自居,热情洋溢地追求玛丽安,在关键时刻却为了五万镑财产背弃了爱情。埃丽诺最后如此概括:“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安适,是他高于一切的指导原则。”(第47章)若说他和约翰·达什伍德有所不同,就在于他尚能为这一选择感到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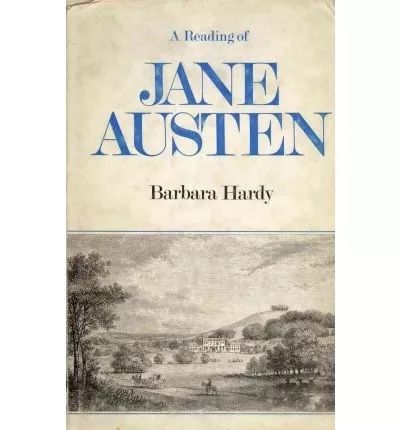
芭芭拉·哈代的《A Reading of Jane Austen》
约翰爵士和他的丈母娘、伦敦生意人的遗孀詹宁斯太太等人也写得各有特点,相当出彩。不过,尽管程度和情况不相同,可以说约翰·达什伍德的思想已在暗中主导这些过渡人物的行为。约翰·达什伍德代表了小说中的“世道”。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性达什伍德们被迫搬家;埃丽诺对爱德华的感情遭到来自费拉斯母女和露西的双重阻挠;玛丽安神采飞扬的初恋最终触礁。可以说,埃丽诺姐妹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约翰·达什伍德和他们所代表的原则所决定的;姐妹俩的共同的人生探索和彼此间的思想分歧也是以那个敛财逐利世界为背景的。巴巴拉·哈代指出,小说中两位女主人公被其他一些人物所围绕,而那些人的情感生活是“败坏的,冷酷的,虚假的”,针对这样一种环境背景,“我们探究真感情的艰难存在”[20]。她对背景的强调可说是切中肯綮。
理智与情感的姐妹“血缘”
《理智与情感》中提到约翰·达什伍德的第一句话是:他“不像家里其他人那样感情强烈”(第1章)。这句话为他定了性,指出他和继母一家的最根本差异在于是否注重感情。小说的标题以及这类陈述点明,叙事将在重感情和不重感情的人的对比和冲突中展开,从而把全书放进了十八纪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思潮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因此,在讨论达什伍德姐妹所代表的“理智”(sense)与“情感”(sensibility)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情感主义的缘起。
“为什么,”有研究者问道,许多严肃文学家都“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纷纷来关注情感呢!”[21]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指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诸国的贵族从武士转化为廷臣,促使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习俗、趣味乃至心理状态趋向于“文雅”和“精致”。[22] “善感”是在国内大规模武装冲突消除后形成的一种现代品性:“现代的安定、闲暇和教育生成了某种细腻的感性和精美的德行……在更严峻的年代里被压抑的人类同情心,特别是对弱者和不幸者的同情,迅速地膨胀,社会良心开始关注囚犯、儿童、动物和奴隶。”[23] 对个人感情的强调与家庭形态调整(向核心家庭过渡)同步。女性地位日渐突出。以理查逊的葛兰底森[24]为代表的新一代“绅士”具有温和细致、善解人意等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专有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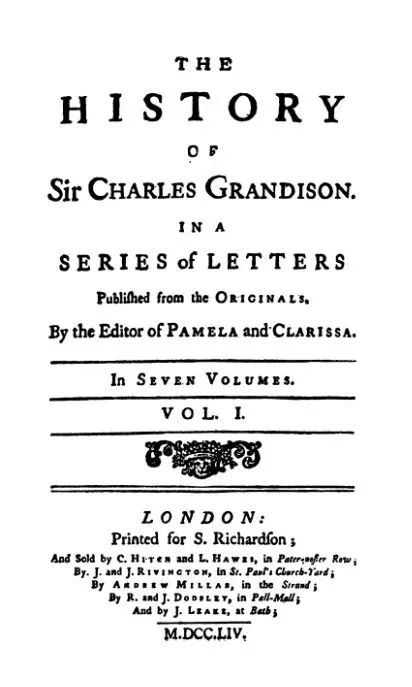
理查逊的《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
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情感主义又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对“现代社会”的有意识的回应、批评或矫正。福柯曾注意到忧郁的泛滥和“商人国家”有某种内在关系。[25] 换句话说,约翰·达什伍德们的敛财逐利行径对人际关系的冲击逼出了某些应对、调整甚至抗争。情感主义思潮最直接最重要的先驱者是洛克的学生、友人和恩主沙夫茨伯里伯爵(本名安·阿·库珀,1671 —1713)。他不赞成霍布斯的人性自私论[26],明确反对“利益驱动世界”的流行观点。著名哲学家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也曾深入探讨人的感觉和感情。“情感”派思想家还常以传统文明为鉴照,批评现代社会使人“失去爱的纽带”,成了“彼此隔离的孤立个体”。[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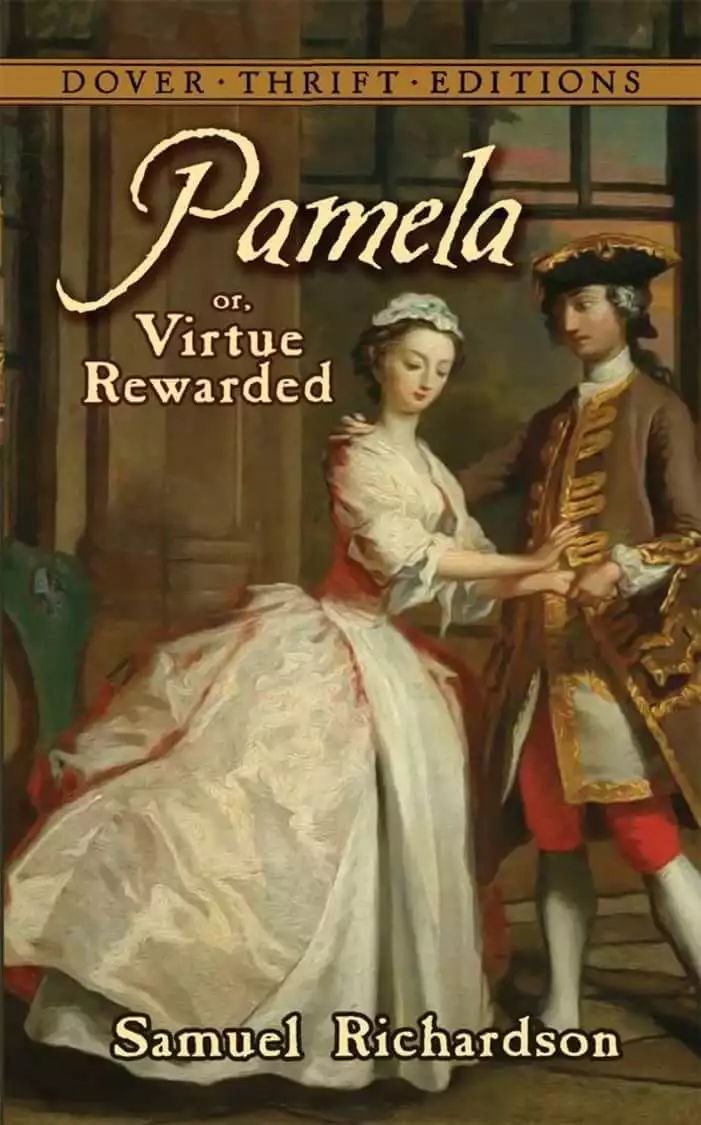
理查逊的《帕梅拉》
在情感主义思潮的播散中,小说起了关键的作用。理查逊的小说《帕梅拉》(1740)问世之后,情感主义和眼泪崇拜在英国迅速成为流行的时尚,讨论“sensibility”和“sentimental”的文章著述层出不穷[28],甚至有期刊索性起名叫《情感杂志》(Sentimental Magazine)。诸多畅销故事,如《素朴儿》(1744)、《威克菲尔德的牧师》(1766)、《重情者》(1773)等等,连篇累牍地罗列天真而善感的主人公们催人泪下的遭遇。这些重情者的被动、无能和失败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世俗能力观和成功观的,以讲求功利的现代人以及浇漓败坏的世风为对照。“情感热”还催生了哥特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沉思忧郁的诗人气质,对废墟遗址的倾心青睐,对山色湖光的沉迷热衷等等,这些先期浪漫主义情调与情感主义趣味共同构筑着当时的文化时尚。
达什伍德太太及其女儿们是“感情强烈”的人。她们是约翰·达什伍德原则的受害者。她们受约翰夫妇排挤,失去亲人和原有收入以后又失去了安身之地。另一方面,她们又是约翰的金钱逻辑的抵制者。她们讲求人际间的亲情、友爱以及必要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牺牲。小说有意细致地描述了她们在逆境中如何搬家、安家并与新邻居们相处,渲染她们一家人彼此依存,相互关怀。
玛丽安有两次在心情沮丧之时碰到爱德华来访,都打起精神来欢迎客人。叙述用揶揄的口吻议论说:“爱德华是普天之下因为不是威洛比而能被宽恕的唯一来访者。”话说得简洁而俏皮,似贬似褒。来客如若不是威洛比就需要“宽恕”,玛丽安渴望见到爱人的情状由此跃然纸上。她沉溺于一己的荒唐之处也被这短短半句话点透,显得颇为扎眼。不过,她毕竟能够跳出自己的感受,能“为姐姐感到高兴”(第15章),因此爱德华的“被宽恕”也使玛丽安因其善良本质而得到旁观的述者和读者的谅解。
在奥斯丁笔下,婚姻是使“利与礼”(Property and Propriety)两大主题纠结在一起的核心事件[29],也是不同人物、不同思想自我展示并彼此角逐的生活舞台和战场。面对婚姻的试金石,达什伍德女性坚守着“情感”底线。她们的父亲至少不完全唯钱是论——虽然头一位太太家资丰厚,续弦时却没有考虑财产。第二任达太太坚持感情至上的观点。她看出爱德华没有经济自立能力,但不阻拦他和埃丽诺的交往,“因为财产不等而拆散一对志趣相投的恋人,这与她所有的原则都是格格不入的”(第3章)。多少得益于这位母亲的调教和庇护,不论埃丽诺还是玛丽安在择偶时都明确地把两情相悦放在第一位。玛丽安直言宣布,出于利益考量而安排的婚事“根本算不上婚姻”,“只是一种商业交易,双方都想损人利己”(第8章) 。埃丽诺虽然被妹妹认为是太务实,太不热烈,其实一直坚持自己的内心感受,不曾因任何经济因素而动摇,后来遭遇露西搅局,仍不肯轻易改变初衷。
她们的态度与约翰·达什伍德及露西们形成鲜明对照。约翰自己娶了阔太太并紧“傍”阔丈母娘,还帮她们两位敲边鼓,力促爱德华与莫顿小姐攀亲。爱德华和露西的婚约曝光后,他又立刻转头鼓吹费拉斯家次子罗伯特和莫顿小姐的婚事。他一本正经地对埃丽诺讲他的想法,后者忍不住插嘴道:“想来那位小姐在这件事上是没有选择权的。”约翰很典型地反问“选择权”是什么意思;然后轻描淡写地继续说:嫁给兄弟俩中的哪一个没有区别,关键只是谁处在继承人地位(第41章)。对于约翰来说,婚姻是公司联营,作为结婚对象的具体个人乃至双方当事人的意愿根本无关紧要,关键是谁是家族财产的法人代表。
在奥斯丁笔下,婚姻市场中的众生都是标了价的。比如,《曼斯菲尔德庄园》开篇就说:仅有7,000镑私产的玛利亚·沃德小姐出人意料地嫁入财大位高的从男爵家,全村人为之惊叹,她当律师的叔叔承认,对应于这档婚事她的身价至少欠缺3,000镑。约翰把所有的人和人际关系货币化的本事绝对不下于那位律师。他看到玛丽安因失恋痛不欲生,马上断定她的“价值”大打折扣,年收入有五、六百镑的男人是否肯接受她已经很成问题;于是他积极地把年收入2,000镑的布兰登推荐给埃丽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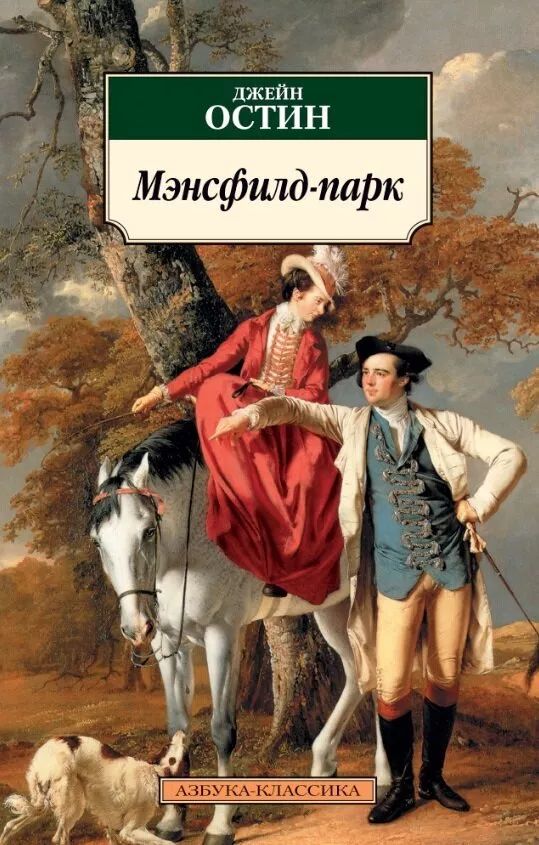
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
而正式加盟“情感”阵营的则有爱德华和布兰登上校。他们像那些典型“重情者”一样,显得“被动”、“无能”。爱德华拒绝“出人头地”,让他的母亲和姐姐痛心不已——他不愿意从政,不谋求发财,也不肯娶家人相中的莫顿小姐,最终选择了没有多少油水的牧师职务和相对贫寒的妻子。被埃丽诺赞为“心地温厚”(第10章)的布兰登对青年时代恋人念念不忘,肩负起照料她的私生女的责任;还把可以卖个好价钱的牧师职位无偿提供给爱德华。
一个很能说明“情感派”行为原则的细节是爱德华和埃丽诺对待露西的态度。爱德华一直在为少年时代莽撞订婚而暗自懊悔,认识埃丽诺后更是如此。然而他却不允许自己毁约,因为他以为露西爱他并一心指靠着他。婚约泄露后母亲向他施压,他本可以顺水推舟甩掉露西,可是他认为,除非露西想要解约,否则他应当一生背十字架,兑现承诺。爱德华的态度有点中世纪遗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虽然很难断定这是能给双方带来幸福的明智决定,却仍不能不从这种把荣誉、责任和对弱势者的担当放在首位的抉择中看到传统道德风范所包含的某种近乎英勇的高贵气度。同样,此时埃丽诺已经明明白白地知道,协助爱德华经济独立很可能就意味着促成他和露西的婚事,使自己的爱情彻底破灭,然而她却按“原则”行事,撇开私念恳请布兰登上校帮助爱德华。
不过,虽然都注重情感、反对唯利是图,埃丽诺和玛丽安的表现很不相同,效果也不一样。英国20世纪前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考德威尔曾说,文艺作品有如梦境,是在思想中进行的代价最小的人生(或社会)试验。[30] 奥斯丁显然有意在这部小说里探讨姐妹二人中谁代表“真感情”,谁对金钱社会的抵制是货真价实而又切实可行的。
小说的叙事围绕她们几乎平行的恋爱经历展开。
17岁的玛丽安率真坦荡,热情奔放,特别讲究艺术情趣和恋人间的心灵相通。她宣布说:“跟一个趣味与我不能完全相投的人一起生活,我是不会幸福的。他必须与我情投意合;我们必须醉心于一样的书,一样的音乐。”(第3章)一天她外出登山遇雨伤了脚,被英俊青年威洛比搭救回家。英雄救美的奇遇让熟读浪漫故事的玛丽安心中生出许多憧憬,和威洛比谈得热火朝天,立刻成了知己。她我行我素,在邻人外客面前无拘无束地和威洛比卿卿我我,又和威洛比一道擅入他姑妈家宅园游玩,并振振有辞地自我辩护说:“假如我的所作所为确有不当之处,我当时定会有所感觉……而一有这种认识,我就不可能感到愉快。”(第13章)拿一己的快乐来证明行为的得当,高度认可人的本能感受及其权威性,她的话正是沙夫茨伯里性善论的回音。
待威洛比突然告辞离开乡间,这位浪漫女孩就少吃不睡,眼泪长流,或不停弹奏、吟唱他们共同欣赏过的乐曲,或独自外出游荡,淋漓尽致地发挥伤别的情怀。玛丽安到伦敦之后再三给威洛比写信却不得回音,痛苦开始变得真实而沉重,最后在一次晚会上的邂逅让她见证了后者的背叛,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与玛丽安不同,埃丽诺“思想敏锐,头脑冷静,虽然年仅19岁,却能为母亲出谋划策。……她心地善良,性格温柔,感情强烈,不过她会克制自己”(第1章)。需要强调的是,这位冷静的姐姐所代表的“理智”和约翰·达什伍德夫妇的算计是两回事。在英语里,特别是在十八世纪,sense一词若取其与“理性”或“智性”相关的含义,几乎等同于good sense或common sense,用于人是指通情达理,思考判断行事中肯合度。对于深受约翰逊博士影响的奥斯丁来说,敛财逐利的贪婪计较压根不能划入“sense”的范畴。因此,叙述介绍埃丽诺时一再提到“心”和“感情”(她母亲评判爱德华时也首先肯定他的“心”),明确标出埃丽诺是在“感情”阵营里,她和玛丽安的分歧乃是同一营垒内的论争。
对于男人,埃丽诺最看重的是人品。她喜欢爱德华不是一见钟情,而是因为两人相处彼此心有灵犀。她意识到爱德华本人态度暧昧似有苦衷,他的家人又在策划有利可图的联姻,因此她非常审慎,坚忍而耐心地等待事态明朗。不想等来的却是露西·斯蒂尔居心叵测的表白。对于埃丽诺,爱德华订婚的消息不啻当头一棒。不过,年仅19岁的埃丽诺有超越一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心胸。她思忖,当初爱德华年少而孤单,露西也必定更单纯可爱些,因而前者的行为并非不可理解。埃丽诺不失礼貌地对待露西并信守保密的诺言;同时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务,送往迎来。只是有一次,她一边暗暗自嘲,一边将詹太太为妹妹准备的号称能够治疗失恋的药酒一饮而尽,让我们窥见了她心里的苦涩和悲伤。
直到露西订婚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埃丽诺才赶紧抢在外人之前向妹妹说明情况。玛丽安正因为威洛比负心而怆痛不已,听了立刻失声大哭。于是,“埃丽诺倒成了安慰者,妹妹痛苦的时候她要安慰妹妹,自己痛苦的时候还得安慰她”(第37章)。该句陈述用的是叙事人低调的中性口吻,只讲实况,不加评说。但是感受却显然是埃丽诺的。这一细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玛丽安那种天真无心的自私:她放纵自己的感受,丝毫没有想到如此行事把额外的痛苦和负担加到了已经备受打击的姐姐身上。另一方面,不过年长两岁的埃丽诺虽然心里痛楚,对妹妹的表现也不那么满意,却仍担起了“安慰者”的任务。这让我们联想到她一向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后,母亲和妹妹一味伤心,在诺兰庄园寄人篱下的半年时间里与哥哥嫂嫂周旋的任务全由她独力担当。母亲看中的房子,她认为“太大住不起”,力促母亲搬到巴顿乡舍。她的冷静务实是不那么有权有势的女性达什伍德们的生存依靠之一。[31] 所以玛丽安会对母亲说:“要是离了她,我们可怎么办啊!”(第3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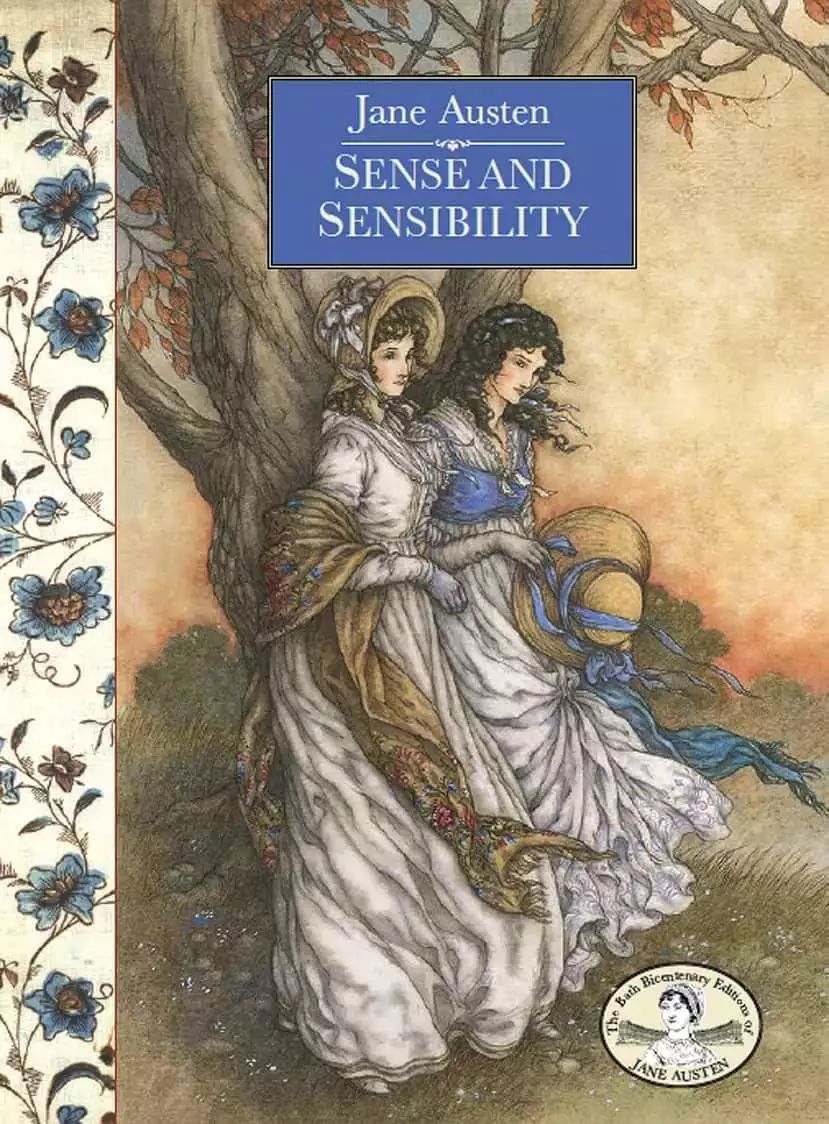
《理智与情感》
如果说玛丽安代表了十八世纪末某些典型的情感主义浪漫姿态,那么她的恋爱挫折以及埃丽诺提供的对照或许可以说体现了奥斯丁对这一思潮的修正或再定位。情感主义讲究同情心,但更强调人性本善并肯定个人追求,几乎不可避免会导向某种唯我主义,背离其反对贪婪自私的初衷。[32] 纯良如玛丽安,一旦她奉行那种认为个人感情和个人追求高于一切的信条,也必然会陷入伤人害己的泥潭。恰如她后来意识到的,她为别人,特别是姐姐和母亲,想得太少了。她看不起詹太太之流,无视社会习俗,并不完全证明她脱俗勇敢,也常常表现了对他人的轻慢和蔑视。
情感主义的自我中心倾向还有另一个深刻的社会根源。如《帕梅拉》一书所揭示,情感主义“美德”是阶级权力再分配中的一种自觉的文化武器,是中等阶级群体和个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争取更大社会影响的方式。正因如此,展示自身的“善感性”常常是一种自我关注、自我赞美、自我提升的行为。比如,由于忧郁和神经质被不少人视作道德敏感性的体现,歇斯底里、哭泣和晕厥便成为许多淑女和准淑女们争相表演的节目。[33] 情感主义时髦迅速沦为一套现成的言论和姿态。“情”的话语如“责任”之类抽象词句一样,已经可以为任何人所用、用在任何人身上。范妮·达什伍德谈到自家儿子和利益,用的是无限夸张的煽情语言。她丈夫约翰议论爱德华不听从母亲安排时责备他不负责任,固执“无情”(第37章)。露西更是开口便大谈她对爱德华以及其他人的深情厚意,以至詹太太夸赞她“很有理智,也很有感情”(第38章)。某些特定趣味更是常常与真正的修养或高尚的情操分家,成为在某些圈子里提高身价的时尚符号。因此,罗伯特·费拉斯张扬他对“乡舍”的喜爱;威洛比熟读浪漫诗歌并时时卖弄,借雪莱诗作把一匹打算送给玛丽安的小马命名为“麦布女王”(第12章)。连玛丽安也未能完全避免自我欣赏和角色意识。她对自然美景的热爱表现得相当外露和夸张。她会高声大气地嚷道:“我以前[在诺兰庄园]……一边走一边观赏秋风扫落叶,纷纷扬扬的,多么惬意?那季节,激起了多少深切的情思?”(第16章)
玛丽安把个人感情和想象放到至高的位置上,后果之一便是缺乏知人和自知之明。用埃丽诺的话说,她缺少“根据常识和观察得出的合理见解”(第11章)。她误读了威洛比和布兰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自己。威洛比并非如她所想是一腔赤忱的重情者;布兰登不是她描绘的乏味老男人;而且她本人也并不那么超凡脱俗。她理直气壮地说:“富裕和堂皇与幸福有什么关系!……宽裕的生活条件就足够了,更多的财富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这话当然不错。不过,当埃丽诺追问她“你的宽裕的标准”时,她竟坦然说:最多一年1,800 到2,000镑(第17章)。玛丽安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有非常具体的物质内容。她希望和威洛比一道居住在乡间宅邸里,被美丽风景环绕,享受音乐和诗歌,有若干仆人,有马有车,还要有男人打猎用的行头和猎狗。比照前文提到的绅士收支状况,可知这属于中等士绅的生活。就是说,玛丽安的浪漫须以相当数量的财产为基础,可是她对此很不自觉,自以为与约翰爵士和詹太太等俗人判若霄壤。与她不同,埃丽诺能够比较冷静地判断自身的真相。这也是她比较谦和,不那么自以为鹤立鸡群的缘故。埃丽诺的“理智”是经过矫正的“感情”,它不仅受责任和理性双重指导,也建立在善于体察世界、体察他人和自己的基础之上。
威洛比的背叛宣告了玛丽安的浪漫实践的失败。由于其无权无钱的地位,她的自私所伤害的主要是她本人。近年对奥斯丁的评论中,有一派强调玛丽安对父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conformity),另一派突出她对社会现状及性别关系现状的批判。其实两面的论证并非水火不容,因为“保守的”奥斯丁和“激进的”沃斯通克拉夫特有很多相通之处。[34] 她们都认为,老一套情感主义话语和姿态已经失效,而且女性由于其弱势地位更易沦为浪漫幻想的受害者。
可以说,存在于埃丽诺和玛丽安所代表的“理智”与“感情”两者间的是姐妹关系,甚至是同一奥斯丁心态的不同侧面。因此,认为姐妹俩一个代表激进的法国式个人主义,一个代表保守思潮,是过于简单化的归纳。两位女主人公的差异和区别是“姐妹内部”分歧,映现了英国情感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埃丽诺的审慎包含了对情感主义的反思,且在另一个层面上构成对约翰·达什伍德世界的更全面的批评。
小小私人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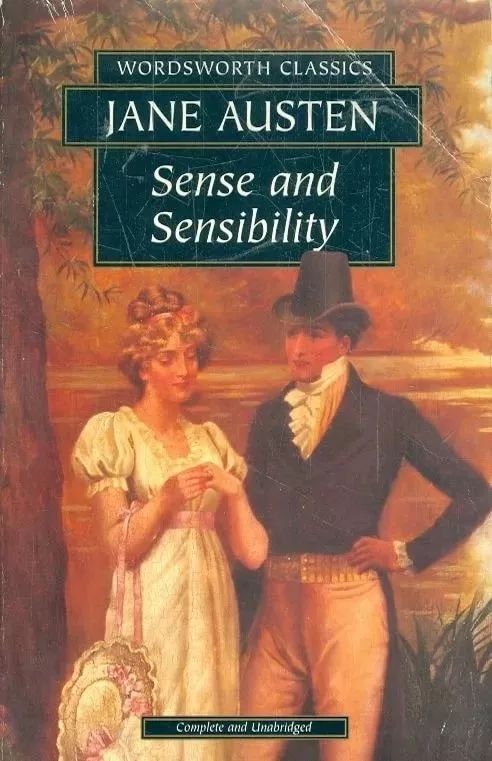
《理智与情感》
大病一场后获得“新生”的玛丽安最终嫁给了布兰登,这时她的人生态度与埃丽诺爱德华们已几乎完全一致。姐妹俩婚后一道在风景如画的拉德福村安居,营造起一个小小世外桃源,一个微型亲情乌托邦。
与此同时,作者严峻的现实主义眼光也使代表正面出路的思想试验被某种冷嘲的阴影所笼罩。前面已经提到,埃丽诺的眼光中包含深刻的自嘲。她敏锐地看出母亲、妹妹乃至自己与大哥约翰和詹太太们有相似之处。后两位一致认为,爱德华的收入不足养家。爱德华和埃丽诺在其他一切障碍都已清除的情况下也推迟结婚——“他们两人还没有热恋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认为一年350镑会给他们带来舒适的生活。”(第49章)这句话包含自我揶揄。的确,他们虽不贪得无厌,却也像约翰们一样明白,结婚是新经济实体的组建,得有适当财力保障其日常运转,还得把詹太太提到的每年添一个孩子考虑进去。[35] 连两姐妹的母亲浪漫的达什伍德太太也有实际的一面,她后来“想把玛丽安和布兰登上校撮合到一起的愿望,虽然比约翰磊落得多,也着实够热切的了”(第50章)。直白叙述把她的态度和约翰·达什伍德相提并论,话音里有明确无误的婉讽。
部分地由于这种洞察,约翰·达什伍德所体现的金钱社会中“亲族相食”(family cannibalism)[36]现象在小说中是用滑稽手法表现的,其可能的残酷后果被淡化,而其荒唐则被拿来观赏取乐。约翰是书中最重要的批判目标,却也是喜剧乐趣的主要来源。有关他的文字是尖刻的,也是宽容带笑的。对露西的处理则远远没有这么大度。第22章开头记述埃丽诺对露西的最初印象,说后者“天生机敏”,但没有受过教育,“粗鄙不堪”(illiterate)。“illiterate”一词口气相当重,有“文盲”之意。这层意思与露西和多人通信的事实相抵牾,自然不成立。但这个词传达了埃丽诺强烈的反感。接下来的叙述称露西在巴顿庄园上上下下大献殷勤的行径“实在太不体面,太不正直,太不诚实”。一连用三个“太不”,激烈的言辞贬斥了露西,也传达了埃丽诺的不快和私见。这类直接评议露西的话虽是从埃丽诺的角度出发,却加盖了叙述者权威认证的印章,如D.A.米勒议论小说另一个段落时所说,在埃丽诺的观察和叙述之间仅存技术性的形式差异,并不含对前者的讽刺。[37]
令人赞叹的是,叙述没有把厌憎转换成恶有恶报的处置,相反却意味深长地给露西安排了大获全胜的结局。她不仅如愿嫁给了财产远多于爱德华的罗伯特,而且最终化解了费太太的恼怒。她的“自私与精明,最初使罗伯特陷入窘境,后来又为他摆脱窘境立下汗马功劳”:

露西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及其获得的荣华富贵,可以被视为一个极其鼓舞人心的事例,说明对于自身利益,只要刻意追求,锲而不舍,不管表面上看来有多大阻力,都会取得圆满成功,除了要牺牲时间和良心之外,别无其他代价(第50章)。

露西的成功是对约翰·达什伍德秩序主导地位的再确认。对此奥斯丁和埃丽诺们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人觉得“这本书的主导基调是阴暗的”[38],并把这种印象归结于玛丽安最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嫁给布兰登的妥协决定。其实“阴暗”不在于玛丽安的个人命运,而在于那个让露西成功、让威洛比背叛、让约翰·达什伍德们得意洋洋的世道,在于正面人物的无能为力。十分耐人寻味,埃丽诺的“喜剧”结局不是她和爱德华争取来的,而是露西自我运作的副产品,是捡露西的“剩儿”。正面人物“消极被动”,其缘由固然与他们拒绝逐利相关,但是作者显然也有意要凸现她笔下的私人乌托邦的偶然性和局限性(否则她可以做别样的叙述安排):它寄生在约翰·达什伍德世界的某些缝隙中,苟存于被后者恩准的一隅。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读者感知到结局的某种“阴暗”,那么批判锋芒和思想之战就仍然存在。有评论指出:奥斯丁把个人经验与其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从而成为“第一位发明适当形式表达对新型社会的批评见识”[39]的伟大作家。可以说,奥斯丁小说自出版以来从未断档,一直被阅读被喜爱,“从不需要被再发现或恢复地位”[40],其根本原因之一正在于约翰·达什伍德们的当代性,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把他们的思想秩序和社会秩序推行到五洲四海。这也是奥斯丁对“铜臭”(brass)威力的描写令二十世纪诗人奥登深感不安的缘故。[41] 不过,奥登们似乎低估了奥斯丁对铜臭世界的抵抗和质问。[42] 她不仅生动地写出了那个世道,还通过埃丽诺们的眼光、叙述的臧否乃至对“大团圆”结局的温情企盼让读者隐隐感到一种持续的压力。小说实际上从绅士世界的内部发起经久的批判,揭示金钱秩序的荒唐和残酷,撒播着对某种变化、某种新乌托邦的渴望,谋求并促进对现代主体和现代社会的修正。
[1]R. W. Chapman ed., Jane Austen’s Letters, 2nd ed. (Oxford:Oxford UP, 1952 ) 401, 469;参看朱虹编选:《奥斯丁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年, 第361-362页。
[2]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Oxford:Oxford UP, 1973 ) 113.
[3]Alistair Duckwor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 1971 ) 一书作者。
[4]参看Marilyn Butler,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Oxford:Clarendon P., 1975 );玛·巴特勒:《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157-171页。
[5]Raymond 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Fontana P., 1976 ) 280 -282.
[6]Clare Tomalin, Jane Austen (New York:Vintage, 1999 ) 155.
[7]参看Frank W. Bradbrook, Jane Austen and Her Predecessors(Cambridge:Cambr idge UP, 1966 ) 28-50。
[8]参看David Monaghan,“Introduction”, in Monaghan, ed., Jane Austen in a Social Context (Houndmills:Macmil -lan, 1981 ) 4 - 6。
[9]Julia Prewit Brown, Jane Austen’s Novels:Social Changes and Literary Form (Cambridge:Harvard UP, 1979 ) 24.
[10]版本为Jane Austen:Sense and Sensibility(Harmondsworth:Penguin, 1967), 全书共50章, 此后引文在正文中只注明章数。译文参照孙致礼译本(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年)。
[11]Ian Watt, “On Sense and Sensibility ”, in Ian Watt, ed., Jane Austen: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Englewood Cliffs, N. J.:Prentice- Hall, 1963) 43.
[12]参看Edward Copeland, “Money ”, in E. Copeland & Juliet McMast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年)135-137。
[13]奥斯丁侄儿曾回忆在那一带农村工业化运作如何取代了妇女手工纺纱, 等等。参看J.E.Austen-Leigh,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Oxford:Clarendon, 1926 ) 41- 42。
[14]在中古时代英国乡村有公地供全村人放牧牛羊等, 自12 世纪以来有权势的个人开始圈占公地。圈地的一个高峰期在1450-1640年间, 所圈土地多用于养羊;另一高峰则在1750-1860 年, 占地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15]R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15.
[16]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第35-36页。
[17]M.M.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trans.C.Emerson & M. Holquist (Austin:Univ.of Texas P., 1981)333.
[18]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四卷第75页。
[19]露西作为一类人物, 其刻画之精彩、内涵之复杂似乎唯有后来萨克雷笔下的蓓基 夏普可比。参看Barbara Hardy, A Reading of Jane Austen(London:Athlone, 1979) 71。
[20]B.Hardy, A Reading of Jane Austen, 41.
[21]P. M. Spacks, Desire and Truth:Functions of Plot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ovels(Chicago:Univ.of Chica-go P.,1990) 115.
[22]Norbert Eli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rans. Edmund Jephcott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 ) 229-333.
[23]J.M.S.Tompkins, The Popular Novel in England:1770-1800(London:Methuen,1961;First published in 1932 )92-93.
[24]理查逊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25]参看Michel Foucault,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Vintage, 1973) 212 -214。
[26]参看Ian Watt, “On Sense and Sensibility”, 44-45。
[27]转引自Jochen Schulte-Sasse, “Afterword”,in Jay Caplan, Framed Narratives(Minneapolis:Univ. of Minnesota P., 1985)102-104。
[28]参看Markman Ellis, The Politics of Sensibility(Cambridge:Cambridge UP, 1996) 5-9, 38。
[29]参看Tony Tanner, Jane Austen(Houndmills:Macmillan,1986), Introduction。
[30]参看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黄梅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59-242页。
[31]参看Ruth apRoberts:“Sense and Sensibility, or Growing up Dichotomous ”, in Harold Bloom, ed., Jane Austen (New York:Chelsea House, 1986 ) 52。
[32]Mary Poovey 曾尖锐指出浪漫爱情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是“非常相容的”, 见Poovey,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en Writer (Chicago:Univ. of Chicago P., 1984) 236。
[33]参看Tompkins, The Popular Novel in England:1770-1800, 102 - 103。
[34]参看Jane Spencer, The Rise of the Woman Novelist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6 ) 168。
[35]简·奥斯丁的嫂子和弟媳中有两位生了11 个孩子并死于难产。参看Tomalin, 277。
[36]Nina Auerbach, “Jane Austen and Romantic Imprisonment, ” in Monaghan, ed., Jane Austen in a Social Context,24.
[37]D.A.Miller, Jane Austen, or The Secret of Style(Princeton:Pr inceton UP, 2003) 21.
[38]Tomalin, Jane Austen, 158.
[39]Ann Benfield, “Jane Austen and the Novel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 in Monaghan, ed., 30.
[40]James Thompson, Between Self and World (Univ. Park:Penn. State UP., 1998) 5.
[41]参看W.H.Auden,“Letter to Lord Byron ”(1937 ),in Auden:Collected Longer Poems(New York:Vintage,1969) 41。
[42]参看Tanner, Jane Auisten, 12。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01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