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马之喻:《理查三世》、人格国家和莎剧舞台上的政治文化转型
编者按
《理查三世》剧末,莎士比亚笔下的英格兰暴君理查三世奔走呼叫:“战马,战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战马!”此语在莎剧释读中常受关注,但它对作品以及当时社会话语的结构意义却未见详论。本文认为无马理查的形象集中体现了早期现代英国政治文化的转型:王国可与战马互换是因为两者同属欧洲中世纪君主实现政治目的和政治存在的工具,而在剧本所处的都铎体制下,君主和国家之间的目的与工具关系面临互换。正是该角色所负载和掩饰的神圣君权和民粹主权这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冲突,使理查三世原本肢体扭曲的驼背造型展示并掩盖了早期现代西方社会话语中意义显著但又极不稳定的人格国家形象,并对当时及后世受众产生了持久吸引力。
作者简介
邹羽,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战马之喻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
作为第一四联剧末篇,《理查三世》是莎士比亚作品中除《哈姆雷特》之外篇幅最长的作品,其主角英格兰国王理查三世也是除哈姆雷特之外剧作家着墨最多的人物。[1] 剧本第五幕第四场展示了英国史上划时代的博茨沃战役片段,学界通常认为此役标志着欧洲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转变,殒命的理查三世也因此成为中世纪英格兰最后的君主。[2] 临近剧终,虽然战马被戮,理查三世仍冒着巨大危险,仗剑徒步,寻机击杀对方首领里士满(即后来的亨利七世),同时呼求战马:“战马,战马,用我的王国换一匹战马!”(5.4.13)[3]。这是该角色在剧中最后一次现身:在第五场中,里士满将宣告他的死亡和国家秩序的恢复。就此而言,呼唤战马的场景堪称理查在莎剧舞台向观众和后世的告别。
《理查三世》采用以都铎立场为写作起点的史料,其褒贬倾向不言自明。[4] 终结于“以国换马”这个荒唐诉求的理查形象,无疑也服务于伊丽莎白一世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5] 二十世纪初以来,几代论者都非常关注此剧:弗洛伊德曾将理查因自身出生状况不理想而产生的怨恨看成人类心理活动的普遍现象[6];现代莎学奠基人之一蒂利亚德则认为,“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显示上帝意志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得到实现”,而理查在此过程中“成了实现上帝意志的工具”(Shakespeare’s:208);戈达德在其名著《莎士比亚之意义》中指出,理查死前的战马呼唤是该剧最发人深省之语,他根据弗洛伊德的阅读,指出战马代表着作为“意识”的理查所无法完全驾驭的“无意识”能量流动[7]。
由于一马之轻与一国之重在直观上差别巨大,两者交换显得突兀,河畔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编者之一勒文因而试图在两者间寻找过渡的必然性,指出当理查“失去骑位,他也将失去王位”(“Tents”: 214);塔格芙虽未直接评论战马呼唤,但也延伸了蒂利亚德之说,认为该剧是莎士比亚演示都铎王朝奠基逻辑的核心作品[8];莫尔顿和伯内特以文本和都铎史料研究为基础,分别论述理查所代表的“失控的男性气质”与国王身体的“生理怪异”(mola或者monster)在当时语境乃至现代西方文化构成中的普遍意义[9];赫伯特则着眼于该剧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以理查三世的良心谴责为例,在伦理学逻辑上推导出政治运作无法回避政治伦理这个结论[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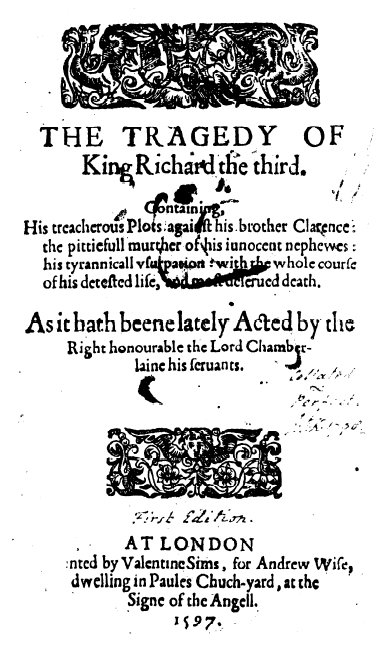
《理查三世》1597年版扉页
在戈达德与勒文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战马呼唤在文本结构中占有关键位置。首先,它与理查在全剧开篇独白所称“让颤抖的敌人吓掉灵魂”、“带着铁刺的骏马”(1.1.10-11)之语相互呼应。在其兄爱德华四世治下的承平时代,理查抱怨战马在君主轻歌曼舞的生活中失去意义,可当他自己成为国王并重新置身战场之际,他却要面对战马被屠(see 5.4.4)和无马可依的境况。其次,在第一幕中,马匹意象在理查的独白中与谋害、错乱和委屈服从共同出现:在图谋克莱伦斯之时,理查希望后者“乘坐传驿兼程归天”(1.1.145);紧接着,他自认在向安夫人求婚时心态过于急迫(see 1.1.159);当他在第三场面对王嫂伊丽莎白时,他又宣称自己为其丈夫的征伐事业“尽过汗马之劳”(1.3.121)。但从第五幕第三场开始,第一幕的多样性铺垫开始向战马意象集中:理查从噩梦中惊醒,第一句话就是“再给我一匹战马”(5.3.175);他给诺福克公爵所下指令也同主力骑兵(see 5.3.298)在战场上的布置相关;直到临阵誓师,他对部伍最后的号召依然是“战斗吧,悍猛的国人,架起长弓,弓手们,将弓引满。用马刺撞击你们骄傲的战马,在血河中驱驰,让尔等的断矛震恐苍穹”(5.3.336-339)。
就舞台动作而言,理查离场前的战马呼唤显然是剧本对角色的战马依赖的最终强调。如果进一步关注第五幕第五场理查梦醒后的那段独白,我们对角色的认识会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既然那段独白体现了理查对自己过往罪恶的悔悟,那么它是否就如勒文所说的那样,体现了莎剧人物得以与同时代的马娄(Christopher Marlowe)等戏剧家笔下角色拉开距离这个特点,即“在既以自身方式存在,又以较为善良的面貌出现之时,每一个恶棍都承担着双重角色”(“Tents”: 202)?或者,还是像戈达德分析的那样,理查的梦醒自责将“惊悚剧中的怪物变为引起我们同情的悲剧形象”(Meaning: 39)?如果进一步探究,那么,追随主流意识形态诅咒都铎建国对立人物的《理查三世》究竟如何在剧中具体引发了观众对其复杂性的兴趣甚至同情?另一方面,该段独白中的某些语句也相当费解,比如“我惧怕什么?我自己?旁边并无别人。理查爱理查,也就是说,我是我[11](5.3.180-181)。在决战前夜的道德反思中,理查身边出现的这样一个“我外我”的影子除了明确预示角色人格的崩溃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含义?
本文从战马呼唤出发,首先讨论战马与王国的交换所揭示的君主与国家的关系,尤其是投射在理查式传统君主和里士满式都铎君主身上的不同政治体想象;其次,根据英格兰早期现代共同体话语的形成,文章试图揭示理查和里士满在剧中凸显的“人格国家”(person of state)这一原本仅通行于政治思想史讨论中的形象;最后,文章试图在当代剧论有关“魅力”的形式分析基础上,呈现人格国家话语在莎剧舞台上的表现结构,特别是它在神圣君权和民粹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之间的平衡对当时及后世西方公众政治文化想象的巨大吸引力。
战争与和平
按剧中描述,理查的直观形象是脊背弓曲、手臂萎缩、行走颠踬 (see “Tents”: 202)。显然战马为理查提供了人体动力学支撑,或者说,理查在剧中对战马的依赖至少部分源于其生理缺陷,所以他在马上比在马下表现得更自如。由此可见,当理查在战马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等值关系时,该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理查与“王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五个直观特点:

理查三世被塑造为驼背、跛足的形象(Steve Weingartner饰,2009)
首先,君主和国家具有特殊的连体性:生理残障使理查对战马产生依赖,因为后者可补其个人身体驱动力之不足;作为僭位者的理查,其身份缺乏合法性这一“政治残障”也使他依赖国家暴力,似乎只有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才能为其僭主身份提供足够的政治资源。[12]
其次,理查治下的国家是一种攻击性而非禁制性暴力资源。他反复提及的“horse”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世纪骑士所用的特殊马种,此类马匹当时价格昂贵,但除了征伐冲杀之外别无他用。[13] 同样,对理查而言,承平时代的马下国家非但无法彰显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优长,反而凸显了其生理缺陷,由于形象丑陋,“狗类见我止足,也会向我吠叫”(1.1.23),只有战时国家才能让他凭靠战马帮助王兄击败各路对手,表现自己的英武杰出。所以,一旦篡位成功,受理查控制的国家力量立即被先后用来攻击以里弗斯勋爵为首的后党、勃金汉叛军以及里士满纠合的新兰开斯特(都铎)团体,直至理查本人殒命博茨沃战场。
第三,就像战马可以在战争中损耗,君主对王国的拥有也并不一定能永久持续。在理查看来,为了战场上的胜利,王国在政治博弈中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筹码或者一项可剥离的资产。[14]
第四,对国家的控制只是构成君主身份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就像骑士一般都掌控战马,国王一般也掌控国家。但仅具掌控战马这一特征并不说明他是骑士,他也可以是马夫,比如博茨沃战前,有人称理查重臣诺福克公爵为“诺福克马夫”(Jokey of Norfolk),即暗示后者可以指挥军队但并不具备最终拥有权。掌控国家的也同样不一定是君主,也可指类似理查篡位前充当护国公角色的这类人物。骑士与马夫、国王与护国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除有暂时支配权外,还有最终处置权。在博茨沃战场上,唯有国王理查方能以国换马,或者说拥有为延续政治生命而冒失去政治生命风险的权力。[15]

历史上的理查三世(1452—1485)
第五,作为都铎主流话语的一部分,《理查三世》通过骑士和战马的譬喻关系负面地烘托了中世纪君主对国家的绝对处置权。作为战马的国家或者国家精英(the political nation),不但受到理查的虐待,也如戈达德所说无法被理查完全驾驭 (see Meaning: 39)。例如,在第五幕第四场战马和国家关系递进为直接交换关系之前,第三场反复强调战马与国家精英的相互等同关系:在即将入睡之际,理查吩咐近侍拉特克立夫次晨为白马萨立装配马鞍(see 5.3.62),而作为王室主将之一的诺福克公爵长子正名为萨立伯爵(Earl of Surrey),作品似乎唯恐观众不明白该伯爵和理查战马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安排拉特克立夫向理查郑重报告勤如走马的萨立伯爵此前如何认真巡营(see 5.3.67-69);次晨,当诺福克公爵前来禀报敌军在战场出现这一战况时,理查的第一反应即是让近侍为马配鞍(see 5.3.287),并对诺福克下达命令,明确“主骑”在战场布局中的位置。剧本安排理查将人畜关系与君臣关系如此相提并论,证明理查轻视甚至虐待国家精英这一君主自身政治存在的保证和政治动力的来源,使得最后一任金雀花王朝君主的君国关系在都铎语境中变得极为丑恶荒诞。同时,剧中理查依仗的其他重臣,如勃金汉公爵及斯丹莱勋爵,也因不堪虐使,在其讨伐里士满的不同节点反戈而击,这不仅预示骑士座下战马的亡失,也喻指国家与君主之间关系的脆弱,表明由政治精英组成的国家不会像战马那样顺服。
相比于理查人马连体的异态譬喻,都铎王朝开创者里士满在剧中虽迟至第五幕第二场才现身,却拥有正义君主的常态形象。从他以“诸位袍泽”(fellows in arms)(5.2.1)称呼其追随者的出场语开始,他就不断强调君主与其随从者之间家人般的共享共存关系。如果理查代表着中世纪骑士对战马的虐待和摧残,因此是恶性的连体,那么里士满就代表着一种善的、回避战马譬喻的连体。
从中古英文的“felawe”和古英文的“fēolaga”来看,fellow一词可以追溯到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的“fēlagi”,该词由词根fē(牛只、金钱)与lag(放置)组成,表明共享与合作之意。在第五幕第三场的战前誓师这一场景中,共享之意被更明确地表述为感谢大小臣工与国与君休戚与共而做出的政治允诺:理查“创制了达到其目标的工具,随之又毁弃了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工具”(5.3.246-247),里士满与其追随者之间却存在着长期共享关系,因为“只要你们与国家之敌作战,国家自会给你们丰厚的回报”(5.3.255-256)。

博茨沃战役,1485年
这样的共享也不同于理查与勃金汉公爵在合作击败伊丽莎白为首的后党过程中的深谋密算和诡异分赃,而是体现出了具有共同体色彩的直接无差别性:“如果上苍眷顾,你们中间最卑微的一员也将分享胜利的果实。”(5.3.265-266)在剧末里士满获胜的场景中,里士满的战争终结宣言不但回到了他出场语中的和平主题,即“这一场流血的激战将给我们带来永久和平”(5.2.15-16),也反驳了理查在该剧开端独白中对战争的怀念:理查抱怨“面色阴沉的战神抚平了(hath smooth’d)狰狞的表情”(1.1.9),里士满则希望“上帝允许两家子孙为将来的日子带去从容的和平(smooth-faced peace),善意的富足和美满的时光”(5.5.32-34)。理查和里士满都用到了smooth一词,但相关情绪对比明显。
在剧场之外的一般社会话语中,战马之喻隐含的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观念与都铎主流话语对政治共同体的强调更是格格不入。将政治群体比作有机体的譬喻源自柏拉图《理想国》及中世纪基督教教义中“视教会为与基督真实身体(corpus verum)相对的基督神秘身体(corpus mysticum)”这一思想[16],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所作《论政府原理》(1159)[17]一书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see King’s: 199)。欧洲中世纪与早期现代关于君主与国家不可分的认识更来自罗马法,如塞内加(Seneca)对尼禄(Nero)的训诲:“尔即国家之灵魂,而国家则为尔之身体。” (qtd. in King’s: 215) 但从兰开斯特时代的重要法学家福蒂斯丘(Sir John Fortesque)开始,英格兰政治话语就开始强调,相对于法国政权集中于国王一人,英格兰政权形式体现为国王、贵族和平民三位一体(trinity)的合成型权威(composite authority),而且“正如人的身体由神经维系,使神秘身体聚而为一的则是法律”(qtd. in King’s: 224)。进入都铎时代后,英格兰社会精英有关政治共同体(commonwealth)构建的关注更从君国一体的神学比喻逐渐进入到显然带有世俗性思考的阶段:亨利七世的酷吏达德利在1509年被亨利八世处死之前,在狱中完成了悔意昭然的《共同体之树》,该书在当时颇有影响;亨利八世的御前大臣莫尔于1516年出版了拉丁文版《乌托邦》,该书虽以假想为媒介,但关注的仍是教俗共同体的合理性与可能性;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前会议成员史密斯爵士于1549年完成了《论英格兰共同体》一书,针对当时英格兰世俗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解决办法;崛起于都铎王朝末期、在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文名大显的培根,在1627年留下了遗作《新亚特兰提斯》这部有关理想世俗政治共同体的未完成作品;斯图亚特储君查理二世在流亡时期的老师霍布斯所作《利维坦:教俗共同体的实质、形式与力量》(1651)更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滥觞。[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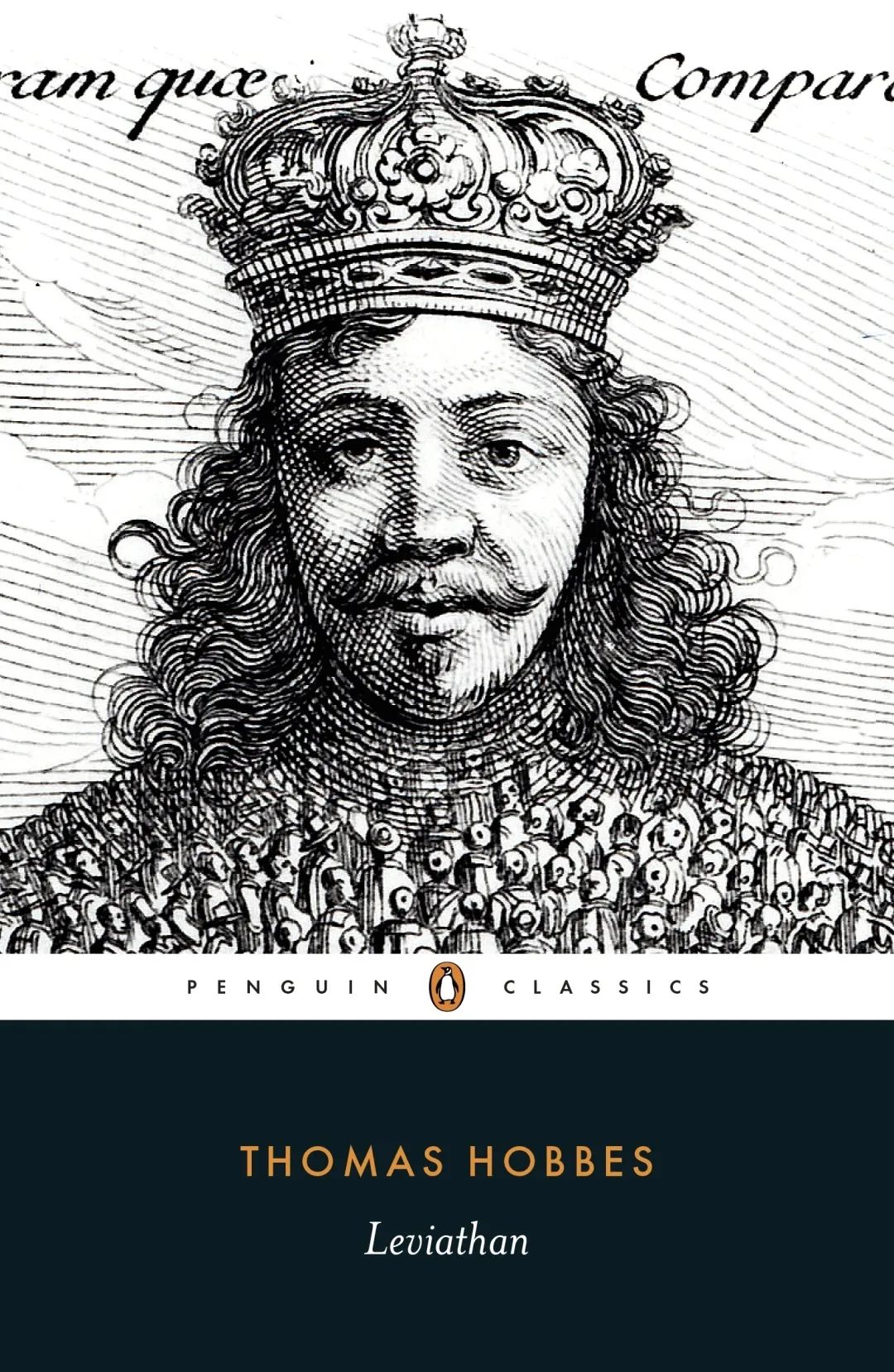
霍布斯的《利维坦》(企鹅版封面)
这些著作虽取向各异、体裁不同,但与理查三世在剧终代表的君主对国家的绝对处置权相比,似乎都有着反向的论述起点,即,现代西方政治的共同体话语使政治体内国王与国土人民关系逐渐紧密。随着都铎王朝兴起,英国十六世纪君主权力开始同国土上的国民、文化、法制、宗教、经济等多种结构深度契合。[19] 如果中世纪政治主权的完整体现为君主对国家的最终处置权,那么从《理查三世》的立场看,理查割弃臣民如走马,而亨利不舍臣民如同怀,不仅指向君主人格或治术的不同,也体现出两种政治体制特别是两种君主与国家关系的范畴性差异。虽然commonwealth或commonweal一词并未在剧中出现,但在幕落之前,舞台上的政治行为主体分明已从篡位后的理查这一非理性和不道德的“前都铎”国君,变成了亨利七世所预示的都铎后期建立在政治理性和政治伦理之上的政治共同体。由此可见,蒂利亚德关于《理查三世》“显示上帝意志如何在英国历史上得到实现”之说虽然偏重宗教立场,但如果用“政治共同体”一词替换“上帝”,原有设定在世俗语境中仍能成立。[20] 换言之,在斯图亚特王朝发生的弑君革命将共同体逻辑推向极端之前,虽然都铎社会并不具备一种舞台话语来完全颠倒理查的政治逻辑,以国家名义处置君主,但里士满作为与共同体一体共生、相互制约的早期现代君主形象,已在虚构舞台上明确定型。里士满所提倡的善的连体明确置换了以人马一体为表征的、政治行为却又自相抵触的恶的连体。[21]
人格国家
即便如此,当我们把注意力从战马意象本身转向与战马有关的剧本叙事结构时,理查与里士满之间的极端对立显然不能直接简化为惩前扬后的都铎主流价值,因为里士满形象背后不仅存在着早期现代国家的影子,这个影子作为不出场的舞台形象也与理查有关。在剧中,理查政治存在的首要目的似乎就是战争。战马譬喻除了指向角色驼背颠行这种形体意象上的扭转,还指向他在舞台动作中的扭转:作为“马夫”(护国公)的理查在篡位过程中智勇过人,但一旦成功“上马”成为国家这匹战马的真正主宰(国王),就立即陷入自取灭亡的疯狂之中。[22] 到第三幕为止,他在作恶的道路上畅行无阻:他陷害其兄克莱伦斯公爵,骗取安夫人的欢心,使重病的国王在自责中咽气,囚杀政敌里维斯侯爵,虏获幼王爱德华五世及其弟小约克公爵,清除意图阻止其篡位的重要宫廷盟友,如海斯廷斯勋爵,并在伦敦市长及其他臣民的勉强拥戴下顺利登基。但在达到成功的顶点后,他所有的政治判断开始接连发生失误:他谋害废王的决定疏离了自己的核心支持者勃金汉公爵,导致后者反叛被杀;他对里士满继父斯坦利勋爵的威逼利诱,效果适得其反,导致他自己在博茨沃决战的关键时刻溃败;他在失去战马后跛行血战,也明显是失智之举,合理举措无疑应该是先求自存,后求杀敌。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传统阅读常将国王理查三世的形象看作莎剧对西方早期现代话语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某种去伦理化的政治理性)的呈现。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作为《理查三世》前奏的《亨利六世》(下)中,理查角色本身已明言,他可以进行各色高明欺瞒,甚至“送那谋财害命的马基雅维利返校进修”(3 Henry VI : 3.2.193);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剧中理查为谋求个人权力而在篡位成功前践踏政治伦理、冷酷算计。[23] 赫伯特即试图在理查的“理性算计”和“非理性自毁”之间的冲突这个基础上,将理查在剧本后半部明显损害其僭主利益的自毁行为归结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伦理意义上的必然失败,但又同时坚持角色的马基雅维利倾向。[24] 但这样的释读不仅简化了理查这一舞台人物的内在冲突,也忽视了他与里士满在都铎晚期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微妙关系。

都铎王朝开创者里士满伯爵亨利·都铎(即亨利七世,1457—1509)
如果按戈达德所言,此剧始终关注“报复”主题(see Meaning: 35),那么剧中理查基于生命不公而展开的报复行为连续涉及敌方、友方和自身三个对象:在消灭敌方(后党首领里弗斯等人)之后,他迅速向友方(朝中的反后党重臣海斯廷斯及支持其篡位的大贵族勃金汉)开刀,在屠戮友方后的第三阶段,理查似乎无法回避与自身为敌,将自身视为诅咒与毁灭的目标。在第五幕第四场中,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与其说是跛行求敌,不如说是自求一死。换言之,自毁也正是该幕第三场理查梦醒自责的延续和外化。在“创制了达到其目标的工具,随之又毁弃了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工具”之时,最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似乎未曾意识到他自己也正是这样的一项工具。因此,在伊丽莎白后期主流政治话语所强调的教俗共同体框架内,理查虽然在作品前半部分与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僭主特质重合,但就整体而言,他不但与人人为敌,具有明显的反共同体倾向,还在作品后半部分表现出与马基雅维利式君主完全背道而驰的自毁热情,揭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永恒战争原则,或者说一种极端与漫画化的、后来在霍布斯著作中得到理论化表述的“自然状态”。
国王理查因此具有早期现代(都铎时代)君主和中世纪(前都铎)君主的双重性:作为前者,他代表着践踏一切传统道德的非伦理政治行为;作为后者,他呈现出永恒战争状态和政治上的非理性。理想化的里士满则在剧中同时解决了前现代政治中的自然状态和早期现代政治中的非伦理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伊丽莎白宫廷所代表的非宗教极端主义国际国内政治[25]在当时的民间宗教情绪异常激烈的语境中极易招致类似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污名。因此,伊丽莎白后期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有理由借助理查这个反面政治形象将所谓的马基雅维利逻辑他者化,但另一方面,若深入追踪这种逻辑,与这一形象持续纠缠,也将不利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如莎剧所示,有效的解决途径反而是将他者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继续改写成与当时社会认同的政治共同体逻辑相对立的非理性君主政治,即与一切为敌但又同时自恨自毁的漫画式政治逻辑,由此,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克服也就因而变成了都铎共同体如何克服前都铎国君对国家的绝对处置权。
里士满虽在剧终也以军事领袖身份建立国家,但他的战争行为和政治存在的目的却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建立具有共同体意义的国家。如果对于理查而言,国家只是战争工具,其永恒面目就是政治暴力,那么在里士满那里,这种君主与国家的主权关系发生了变化:共同体意义上的稳定国家已不再只是国王行为的工具,而开始成为目的本身,正如在博茨沃战场上,里士满已无法像理查对待战马一样将国家视为实现君主独立政治目的的筹码。作为君主,里士满的政治存在不仅有必要服务于国家,其自身政治目的也无法独立于作为政治目的的国家。借用十七世纪后期政治哲学家洛克针对英国另一场政治危机的语言来说,国王(里士满)和暴君(理查)的差别就在于“前者以法律为其权力范围,以公众福祉为其统治目的,而后者则使一切都服从于其意志和愿望”[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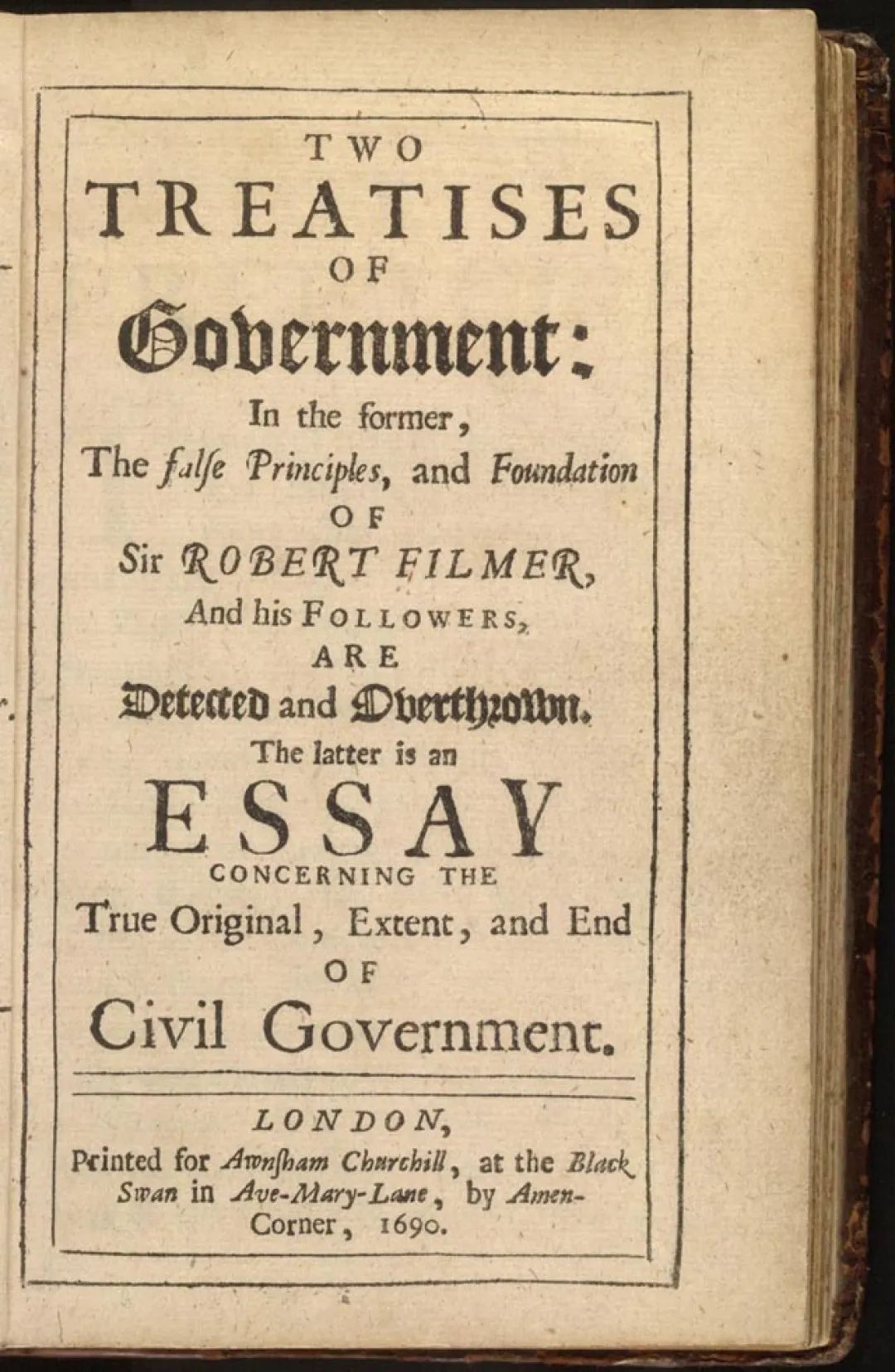
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版)
然而,同理查代表的恶质主权关系相比,作为共同体国家正面形象的里士满在剧中苍白单薄。在戈达德所谓的“充满活力”(gusto)( Meaning:35)的舞台恶人理查之侧,里士满的发挥空间极为有限。与作品中大幅度展开的以理查为代表的中世纪永恒战争主题相比,里士满召唤并实现的都铎和平匆忙急促,草草收场。纵观全剧,理查的形象并未完全被剧末的里士满形象所遮盖和抹除,反而在里士满的反衬下更加令人难忘。那么,作品对都铎主流话语的支持是否因此受到了削弱?究竟是如某些论家所言,《理查三世》仅为剧作家未成熟作品,存在缺失,不值深究,还是如其他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剧作家对当时政体暗怀抗拒,因此善恶对立的里士满与理查在作品篇幅上的倒置可能寄托着某种批判性?[27] 但根据蒂利亚德对里士满剧终演说的阐释,上述两种阅读显然都未能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即“里士满最后演说中的每句言辞,虽然今天看来只是称职的套话,却会让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感受狂喜”(Shakespeare’s : 201)。换言之,剧中都铎王朝奠基人一方面形象苍白,另一方面却具有极大感染力,而作品的真正成功和特异之处不仅在于以浓墨重彩展示理查之恶,营造恶之“活力”,也在于以寥寥数笔激发起观众对都铎主流话语的热烈认同,以扁平形象带来善的“狂喜”。
站在当时观众的立场上,里士满这个角色在1590年代初的伦敦舞台上的宣示无疑戏剧化地重复了其孙女伊丽莎白女王于1588年在提尔伯里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入侵时说出的那段传奇性战前誓言:“为使国家不至因我受辱,我将亲自拿起武器,我将亲自成为你们的将领、审判者和每一次战场成就的奖赏人。我知晓大家已整装待发。你们的表现已经值得贵如王冠的崇高奖赏,而我在此以王者之言保证,你们必将受赏。”[28]但要在跨越历史的语境中认识《理查三世》的持久戏剧魅力,我们就必须透过这一表层的历史事件关联去把握里士满形象的深层结构特征。
要在蒂利亚德提示的基础上阐释两位国王之间超越舞台对峙的历史性关系,一个有效途径显然是将里士满的剧场效果视为来自他背后的某种超越了一时一地的力量,即将其舞台存在解释为一种代表或再现。该力量的震撼作用使得作品在未给予里士满角色充分表现空间的情况下,仍然让他在当时、后世及跨文化观众的心目中留下了足以与理查抗衡的深刻印象。按照当代政治思想史学者斯金纳对霍布斯的解读,我们或可认为,莎士比亚舞台上呈现的里士满与国家的关系代表了霍布斯近六十年后在《利维坦》中以理论语言提出的主权者(sovereign)与共同体(commonwealth)之间的关系。《利维坦》的共同体国家无疑是对理查式“永恒战争”这一自然状态的制约,而里士满呼吁的永久和平则表现为一种人为但必须的秩序。
此外,斯金纳还整理了中世纪后期至早期现代时期流行于意大利和英国的宗教与政治话语,从中概括出聚焦于神圣君权、民粹主权和人格国家这三个不同观念的国家理论,并特别强调霍布斯对于人格国家立场的坚持。他指出,与互为直接矛盾的神圣君权观及民粹主权观不同,霍布斯承继前人,认为国家主权既不从属于世袭君主,也不能被还原为构成国家的民众权力,而是由多元状态下的民众让渡到一个人造之人(Homo artificialis)身上的统一力量,这个人造之人就是具有统一意志的共同体国家。不论主权者以个人还是群体形式出现,都仅是这个虚拟人格国家的代表(see Humanism: 220-221)。[29] 至于主权者如何代表国家,斯金纳则进一步从霍布斯对拉丁文“代表”(representare)一词的舞台解释出发,区分了它在古典时代与基督教时代的不同意义,指出它在古典时代较多地呈现“代替”(standing for)之意,而在基督教时代则更倾向于“代理”(acting for)之意。在政治话语框架内,主权者代表共同体国家的具体方式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他承当并支持着作为国家的那个虚拟个人”;用斯金纳更为明确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作为虚拟个人的共同体国家原本无法实现它作为个人的行动和言语,主权者则赋予了它行动和语言的能力(see Humanism: 358-360)。[30]

亨利七世孙女、伊丽莎白一世女王(1533-1603)
就英国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政治转型而言,斯金纳对人格国家的重视既补充了坎特罗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依据基督教神学对主权者身份二重性的解释,也修正了韦伯在《作为召唤的政治》中有关现代政治祛魅的认识。坎特罗维茨指出,中世纪欧洲国王与基督之间存在相似性,他们都具有驻世和恒久这两种身份,相对于驻世而期限短暂的肉体,国王所代表的国家则包含制度的恒久性。韦伯虽将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绝对国家制度下拥有政治工具的魅力型君主与现代政治中仅仅代理国家权力的祛魅型政治人物区分开来,但却未能充分认识到主权者与人格国家之间的差别,其结果就会导致在中世纪和绝对国家体制下将主权者魅力误认为国家政治本身的魅力,而将现代政治生活中职业政治人本身的祛魅误认为人格国家的整体祛魅。[31]
在英国本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斯金纳的人格国家论能帮助我们更明确地把握霍布斯与洛克国家理论之间的过渡关系和异同。从霍布斯的角度看,洛克一方面将共同体对所属个人的保护落实为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又解除了人格国家这一虚拟“人造之人”对共同体内个人的整体权威。[32] 更重要的是,洛克提出了私有财产的“劳作”生成论,即个人只需通过在某些公有物上加以“劳作”即能使之与其他公有物脱离,变为个人财产。霍布斯的人格国家思想恰恰是通过强调君主对国家的代表和代理权来说明君主对国家不具有类似的对私有财产的支配权。就理查篡位而言,按洛克的逻辑,虽然篡位因强占他人权利而产生不义,但就为获得王位而付出大量“劳作”这点来说,理查将之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在战场上以国换马,似乎也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从霍布斯的角度看,理查篡位本身(从“合法”代理到“不合法”代理)的严重性显然次于其暴政(从代理到占有)对国家的私产化。[33]
此外,斯金纳的霍布斯人格国家论也使主权者所代表的国家脱离了神学话语的支撑,而在世俗意义上具备了说服力。他承接《利维坦》将现代国家作为“世间神”与“不世神”即基督教上帝相对应的思想,说明在早期现代英国社会话语中,共同体国家无需借助神学永恒信念,也可与主权者个人保持距离。同时,由于在主权者与人格国家之间进行了区分,斯金纳笔下的霍布斯也独立于洛克和韦伯立足理性经济生活而展开的国家目的与个人伦理的论述,为现代政治本身留下了魅力空间。[34] 落实到《理查三世》本身,斯金纳的霍布斯人格国家论更为释读里士满这个角色提供了一个走出表层形式瓶颈的关键思路。如果角色的感染力和扁平构成看似相互矛盾,那么里士满在剧中的意义即在于他展示了当时社会话语中人格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微妙关系。作为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里士满在其孙女伊丽莎白统治后期的公共舞台上不仅是共同体国家的实现者,更是人格国家的代理人;他不仅使共同体国家这一“人造之人”获得了行动和言说的能力,更以后者名义实现了自己的行动和言说。[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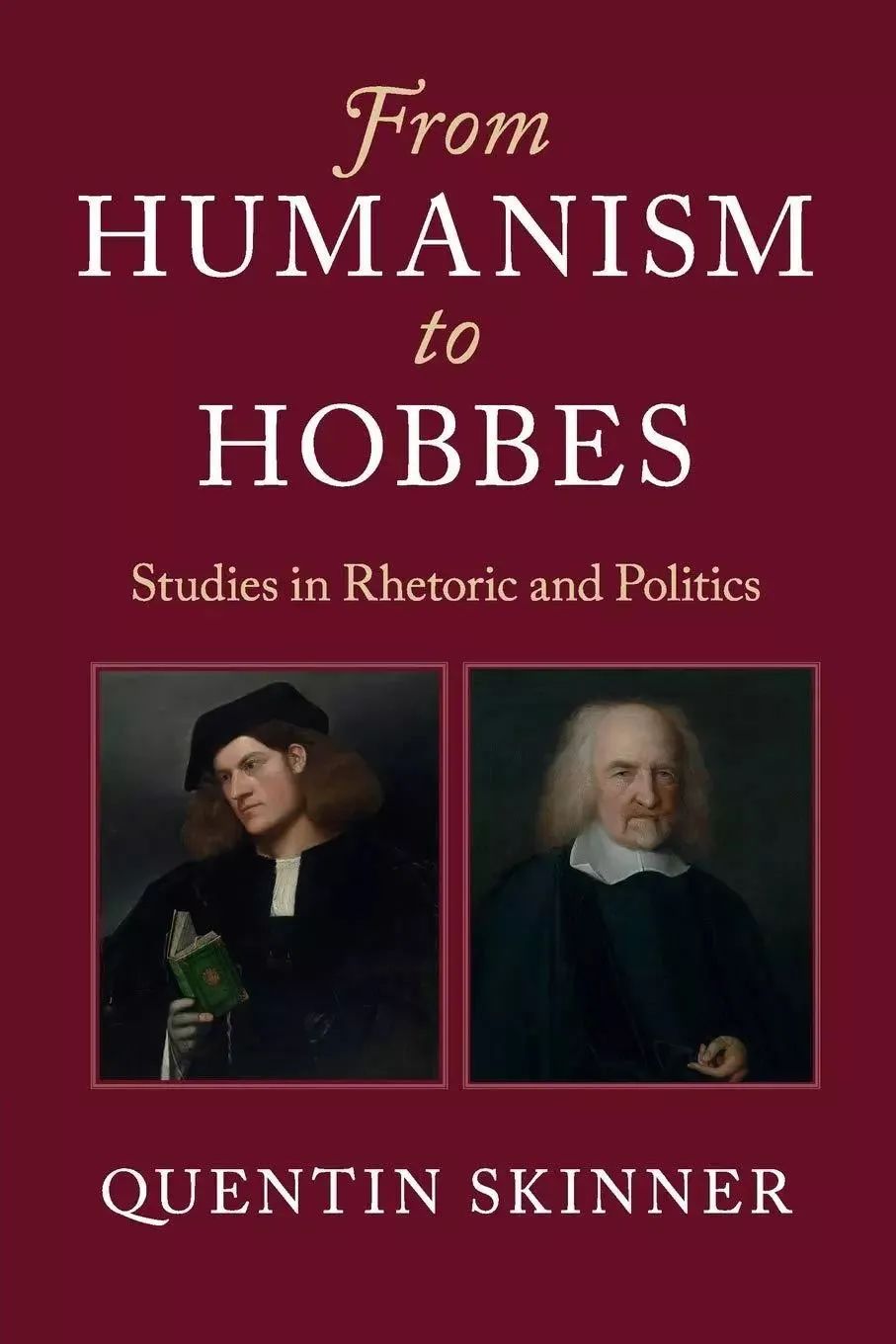
昆廷·斯金纳的《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修辞学与政治》(2018)
肢体扭转
关于舞台魅力在西方戏剧传统中的形式构成,当代戏剧理论家罗奇指出:“魅力即是一种看似毫不费力的同时体现矛盾品质的力量,如强大与虚弱,天真与世故,独特与普遍。具有魅力的人物在这些相互排除的选择之间保持着危险的平衡,就像走钢丝时以一足站立于倾覆之点的舞者。正是因为期待着似乎不可避免的倾坠所产生的特殊紧张感,人们才屏息观看。”[36] 在舞台造型传统方面,罗奇指出:“在古典欧洲戏剧中,这样的对立乃至抗阻由肢体扭转(contraposto)一词传递。它描述表演者同时在膝部、臀部、肩部和头部朝不同方向扭转的姿态。”(It : 8)[37] 就最直观的感受而言,这个原本描述人物矛盾品质的舞台造型在理查身上极具意义:由于脊背弯曲,他的舞台形象本就固定在朝着不同方向的生理扭曲之中。[38]在剧本中,特别是从第五幕第三场起,随着理查的个人形象与战马的关联变得越来越紧密,其生理姿态的扭曲在比喻意义上更延伸为国王在舞台上缺席的马上形象与在场的无马形象(即勒文所谓“其尽人皆知的无马状态”[“Tents”: 214])的二元性:在此,强大与虚弱、幸运与不幸、平衡与倾坠,或罗奇所说的魅力点(charismata)与缺损点(stigmata)对抗而共存(see It : 36)。[39]
如据此将里士满看成剧中理查魅力的苍白陪衬,则未免失之仓促,因为一旦看到里士满背后作为“人造之人”的共同体国家,我们即可觉察里士满魅力的深层来源和独特性。如果把斯金纳提出的早期现代英国社会话语中的人格国家形象放到罗奇的阐释结构中,那么只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形象作为不出场的角色出现在里士满身后,我们就可指出,它在民粹主权和神圣君权这两种政治认同之间的平衡构成了另一具与理查因脊背弯曲而被锁定的舞台造型相对应的扭转肢体(counterpoised body)。莎士比亚在都铎主流话语框架中展示的共同体国家之所以呈现出超常的吸引力,是因为它本身就处在西方早期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这一“吊绳”上,平衡于民粹主权和神圣君权这两种极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政治认同之间,是一个肢体扭转的“人造之人”。至于剧中新王里士满,其吸引力在这里自然无法等同于国家共同体作为肢体扭转人格的魅力,因为在罗奇的分析框架中,他仅是魅力本源的“人偶”(effigy)式再现,为观众提供了对魅力的间接性体验(see It : 28)。
在莎士比亚崛起于伦敦剧坛并服务于御前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的时代,英格兰的剧本审查制度已十分成熟。根据克莫德的论述,时任娱乐总管(Master of Revels)和戏剧审查官的蒂尔尼(Edmund Tilney, 1574—1610在位)权力巨大,他可以“在全英格兰,在国家赋予的特权和一般权力内外,通知、命令并指定任何一个演员、剧团及其戏剧作者携带已经就绪并可即刻上演的相关喜剧、悲剧或表演节目,出现在他本人面前,无论他们是否从属于任何贵族,是否拥有演剧特许还是仅有特许名号,无论他们是喜剧演员、悲剧演员、场间休息时的表演者还是其他形式的表演者,是临时演员还是职业演员”[40]。但这样的国家审查压力毕竟有限,因为当时女王热爱戏剧[41],戏剧作品中被禁止上演的并不多。对于戏剧团体和戏剧文化而言,更大的威胁来自具有保守趋向的其他社会力量和地方政府。在伦敦市长和市府官员1597年向英格兰枢密院提交的呈请中,戏剧的罪行是“除渎神的传闻、淫荡的事迹、骗人的把戏以及羞辱正行的作为外,一无表现。而此等内容的传递方式也绝非规劝大众避免舞台上出现的错恶,而是鼓励模仿。其造成的不良后果甚多,尤为重要的是使得本市内部与周边心存邪念和肆无忌惮的社会渣滓得以扎堆聚啸,共逞猥亵不良之图”[42]。
从更宽泛的文化话语结构来看,1588年英西战争后,由于女王日渐年迈且未婚无嗣,英格兰政治在王位继任和国教延续方面的危机日趋严重,任何对于都铎正统和主流宗教的公开言论都变得极为敏感。伊丽莎白的情报首脑和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虽于1590年辞世,但他从1560年代末期起为防止天主教复辟而创建的现代国家侦查制度对社会的渗透力仍然不可低估。一位名为贝恩斯(Richard Baines)的告密者就曾在1593年上报剧作家马娄的种种出格言行,其中有一条便是:“摩西只是杂耍好手,雷利爵士手下那个哈里茨比他更有能耐。”[43] 在此状态下,都铎晚期剧坛对于亨利七世正面形象的维护似乎也令其舞台形象的单一扁平化变得不可动摇。

伊丽莎白的情报首脑和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爵士(1532?—1590)
有关中世纪戏剧中扁平人物形象的寓言意义和它所蕴含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瓦尔特·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一书中已有深刻论述,而之后施米特从《哈姆雷特》出发对扁平人物的点评更鼓励读者从政治哲学角度重新评估莎士比亚戏剧。[44] 就《理查三世》中的里士满角色而言,莎士比亚做出的应对显然是延续了欧洲中世纪传统中道德剧的普遍实践,将该角色打造为社会大众习惯接受的寓言形象,以同时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城市观众的娱乐要求。[45] 但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也对此舞台程式进行了重要修改,在扁平化的君主形象背后引入了一个若隐若现的人格国家形象,在伊丽莎白后期日渐严苛的反戏剧氛围中,这可以说是一种深度的形式创新。
在1990年代以来有关戏剧和身体表演的研究语境中,对扁平形象的探讨有了进一步发展。比如科学文化研究者巴乔利从科学哲学和科学人类学中经常用到的黑箱化(blackboxing)概念出发,重新思考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与费依拉本德对文化能力的论述,特别围绕伽利略与十六、十七世纪意大利宫廷仪轨,提出了现代科学文化中被身体行为模式充分内化而无法在语言层面得到客观表述的“超然中立感”(sprezzatura, nonchanlance)。[46] 根据对莎剧寓言使用的相关研究,本文倾向于认为,都铎末期英格兰剧场中的普通观众对道德剧寓言的接受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剧场能力,这样的能力往往由于意识形态作用而被观众身体行为充分内化,且无须在体制性话语中充分展开,但却并不缺乏其内在的与当时意识形态并不完全一致的历史丰富性。当代西方戏剧表演理论奠基人谢克纳在表演美学方面的基本论述,正可为展示寓言剧中被黑箱化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提供本雅明历史思辨以外的剧场分析语汇。谢克纳指出,“观察世界各地的表演,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程式。表演者或做‘减法’,取得透明度,消除自己‘创作中因自己生理机制造成的阻碍’(格罗托夫斯基语);或做‘加法’,变得比不在表演状态时更复杂,或与之不同。用阿尔托的话来说,就是他或者她变成了‘一身二体’。前一种技巧为萨满采用,是为狂喜(ecstasy),后一种见于巴厘岛舞者,是为附体(trance)”[47]。在西方戏剧传统中,谢克纳更将这两种舞台程式归类于格罗托夫斯基“贫穷戏剧”所推崇的“神圣表演”和斯塔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所注重的“性格表演”。[48]
据此,勒文那篇著名文章的题目《博茨沃战场上的两座行辕》首先获得了新的阐释角度。按勒文原意,莎士比亚历史剧是对文艺复兴前西方剧场中悲喜剧二分结构的重塑,而悲剧主题人物理查与喜剧主题人物里士满这两座行辕的互动正是对此项重塑的展开(see “Tents”: 199-216)。从谢克纳的角度理解,《理查三世》中新旧二王在面对当时的观众时,还分别代表着性格表演和神圣表演这两种基本舞台程式的建设。如果戏剧舞台上理查的半人半马形象反复显示出该角色人格中的某种非人因素的叠加,那么里士满出场后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竭力约减其本人在代表人格国家形象时可能造成的干扰和阻碍。与理查“恶魔附体”的形象相对立的,正是里士满这个“透明”角色的“神圣宣言”所带来的狂喜。而就作品整体而言,与其说里士满的简短出场为理查跌宕的生平提供了陪衬,不如说理查在舞台上的具体恶行和所遭受的惩罚积极烘托了舞台背后那个不出场的、肢体扭转的都铎国家。莎士比亚历史剧通过“狂喜表演”对“附体表演”的救赎,使得人格国家作为历史制度的不稳定平衡转化成了理查作为舞台人物的不稳定平衡,或者说它使得都铎主流话语中不可言说但具有根本意义的不稳定性(亦即里士满作为共同体化身的伪托性)转化成了当时舞台上可以控制并且解决的不稳定性(亦即理查作为神授君权代表的不合法性)。

萨姆·门德斯指导的《理查三世》,由凯文·斯派西饰演理查三世(2011)
就文本而言,这也为理查这样一个都铎主流话语中的绝对反派为何能以悲剧方式获取同情并在舞台上展示“我外我”的幻觉提供了答案。理查的肢体扭转或者说其性格多面性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他显而易见的扭转表演(半人半畜、既强又弱)不仅同时显示并掩盖了里士满身后那个人格国家的隐含性扭转表演(在神圣君权和民粹主权之间的不稳定),也影射着里士满本身那种半隐半现、似是而非的扭转身份(作为媒介角色之单薄渺小和其所传递背景之深远宏大)。
罗奇分析中对于“魅力国王”(the It King)的认知在此也需获得修正。仅仅将现代西方有关个人魅力的话语从当代美国好莱坞娱乐业追溯到复辟时期那位游戏人生、回光返照的绝对君主查理二世的宫廷显然是不够的;就《理查三世》而论,英国早期现代的魅力话语显然起源更早,且层次更加丰富。当然,根据斯金纳整理的霍布斯人格国家理论,我们也可同意罗奇的部分立场,即认为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转变构成了现代政治魅力的开端而非韦伯所说的终结。同时,我们必须把这一开端还原为里士满背后那个早期共同体人格国家的出现,而非理查式中世纪国家或者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式绝对君主制度的结束。《理查三世》有着两位国家(称职与非称职)代表者,成为复合体的“性格”魅力表演者理查无疑在剧终让位于类似透明人的、传导着人格国家魅力的“神圣”表演者里士满。
结语
作为里士满的前导、陪衬和掩饰,理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作为舞台上的魅力角色,两者的舞台造型往往同时具有至少两种对立面向。这样的多面性也反映了英国从中世纪到早期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困难和挑战。格林布拉特曾在论《奥赛罗》时顺带提出,理查三世这个角色是《奥赛罗》中的反派角色伊阿古的前身。[49] 具有特殊的“越界感知”或“共情”能力的伊阿古,在自塑和自毁的平衡意义上与罗奇的魅力分析相吻合:伊阿古能够侵入他人话语,替代其原有主体,最后不但毁灭话语的原有主体,也毁灭他自己。[50] 但同时,“自我塑形总是和某种危险,某种自我的隐匿、破坏或者丧失体验有关”[51]。按此分析,理查在剧中对安夫人的哄骗、对玛格丽特王后诅咒的回击以及对海斯廷斯、勃金汉公爵、萨立伯爵等所有随从者的利诱威逼,都涉及隐匿自身、进入他人话语,亦即进入“非我”状态的情形。
在理查的剧末呼吁中,我们看到了他最后的自毁。从其梦醒后的“给我一匹战马”到赴死前“用我的王国换一匹战马”,语句的结构发生了实质变化:前者为一般祈使句,后者在《利维坦》意义上显然企图订立一项难以完成的信约。而未能完成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缺乏信约的保证和执行,或者是因为订立信约的对方并不存在,也是因为即便在博茨沃战役的紧要关头,当理查充分展示了霍布斯信约所预设的最为基础的人类共情理解,亦即人类在永恒战争条件下对自我保护的需求时,他仍然不可能成为当时政治话语中约定俗成的缔约人。

亨利·都铎战胜理查三世加冕为王
正如霍布斯所示,主权者是信约保证者而非信约缔结者,换言之,国王只能代表人格国家,不能成为缔约人。当理查主动将自己从信约的裁判和保护者降格为缔约人时,他显然也在建立他代表国家的国王身份以外的另一身份。“以国换马”的最终意义因此演化为“王亦非王”或“一身二体”,并将坎特罗维茨提出的“国王的两个身体”在理查个人和他所代表的国家这两极之间通过上述不可遏制的战争原则推向实质性的断裂乃至毁灭。但纵观整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在其篡位和自毁过程中,脊柱扭曲、半人半马的僭主理查从未违背“我亦非我”的根本“共情”逻辑。
如果理查因试图代表那个他无法代表、无法与之发生共情关系的一部分自己而成为剧中最为尽职的演员和典型魅力人物,那么面目苍白、情绪高昂的里士满对周围政治精英的“越界感知”则因其巨大成功而变得昭然若揭,当然也严禁非议。作品在指出理查不具备神圣君权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隐约寄托在里士满身上的民粹主权归诸荒诞;同时,那些当时观众所熟悉的基督教义中犹大和耶稣形象的附体和狂喜、犯罪与救赎等对立表演程式也并未因此弱化。相反,这些程式因为舞台核心人物的带动,使得其他角色似乎也连同观众一起,被悬置在贯通整个剧场的那个极端双面向的魅力体验之中。在终极意义上,戏剧魅力不只属于舞台,而是要点燃整个剧场的魅力感受,让其中所有人都相互传染,成为焕发魅力的主体。
莎士比亚以后的英国政治文化转型,其实正围绕着剧中缺席但又为之提供终极魅力来源的肢体扭转式人格国家展开。十七世纪英国在绝对君权和民粹主权之间的危险平衡与血腥摇摆,或许正是英国政治共同体意志在历史中展开的内容,它也是无马的理查既预示又掩盖的内容。
[1]See Harry Levin, “Two Tents on Bosworth Field: Richard III, iii, iv, v”, i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18(June/September, 1991), p.203.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Tent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关于博茨沃战役(Battle of Bosworth),详见A. L. Rowse, Bosworth and the War of the Roses, London: Macmillan, 1966;关于英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之间的断代问题,详见Robert Bucholz and Newton Key, Early Modern England 1485-1714: A Narrative History,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09。
[3]See William Shakespeare, Richard III, in Stephen Greenblatt et al., eds., The Norton Shakespeare,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6, pp.555-647.后文出自同一剧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引文在该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中的幕次、场次和行数,不再另注;后文出自诺顿版的注释,将随文标出该版本名称简称“Norton”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后文出自诺顿版其他莎士比亚剧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剧名称及引文所在幕次、场次和行数,不再另注。《理查三世》剧本汉译参考了方重译本(莎士比亚《理查三世》,方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译文有改动。
[4]关于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历史素材来源,详见E. M. W. Tillyard,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4, pp. 21-7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hakespeare’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同理查三世相关的史实,可参见Michael Hicks, Richard III: The Self-Made K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5]第一四开本对此剧介绍如下:“国王理查三世之悲剧:内容包括险恶谋害其兄克莱伦斯、惨杀无辜侄儿、僭越篡位、一生无耻乃至恶贯满盈。”(Norton : 544)
[6]See Sigmund Freud, “Einige Charatertypen aus der psychoanalytishe Arbeit”, in Sigmund Freud, Gersammelte Werke, eds. Anna Freud et al., Band X: Werke aus den Jahren 1913-1917, London: Imago Publishing, 1946, SS.364-391.
[7] See Harold Goddard, The Meaning of Shakespeare,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38-3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Meaning”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8]See Ramie Targoff, “‘Dirty’ Amens: Devotion, Applause and Consent in Richard III”, in Renaissance Drama, 31 (2002), p.64.
[9]See Ian Frederick Moulton, “‘A Monster Great Deformed’: The Unruly Masculinity of Richard III”, in Shakespeare Quarterly, 47.3 (1996), pp.251-268; Mark Thornton Burnett, Constructing “Monsters” in Shakespearean Drama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65-94.
[10]See L. Joseph Herbert, “The Reward of a King: Machiavelli, Aquinas, and Shakespeare’ s Richard III”,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44.4 (2015), pp.238-246.
[11]在第一四联剧中,此语是《理查三世》与《亨利六世》(下)的联结点,因为在后者剧末,类似话语也出现在理查的旁白中:“I am myself alone.”(3 Henry VI: 5.6.83)”
[12]戈达德认为,理查所说的马可与希腊神话中展翼神马Pegasus相比(see Meaning: 39);本文根据理查对战马的依赖,认为理查在剧中似具有半人半马或半畜半人的潜在形象,即希腊神话中的人马怪centaur或者更为贬义的半人半兽的森林神satyr形象。此种形象在下文提及的谢克纳表演分类中具有特别意义。
[13]关于中世纪英格兰蓄马史,详见R. H. Davis, The Medieval Warhors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89; Charles Gladitz, Horse Breeding in the Medieval World,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7; Ann Hyland, The Warhorse, 1250-1600,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Ltd., 1998。
[14]有关诺曼征服以来、特别是金雀花王朝至都铎王朝期间英格兰国家制度的形成,详见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第三版将“Jokey of Norfolk”改为了“Jackie of Norfolk”(5.3.302), 与第一四开本有异。但改动后此语失去了与上下文之间的关联,故本文据第一四开本改回。按照当代学者斯金纳对格劳休斯相关政治学讨论的归纳,国家的政治使用权和拥有权之间的区别可表述为:“绝对王权主义者未能认识到以下这点,即,主权者的概括表述是,作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对国家并不拥有充分财产权,而通常只拥有使用权。”(Quentin Skinner, From Humanism to Hobbes: Studies in Rhetoric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4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Humanism”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See Ernest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94-231.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King’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7]See 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 ed. and trans. Cary J. Neder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8]See Edmund Dudley, The Tree of Commonwealth: A Treatise, ed.and intro. D. M. Brod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Thomas Moore, Utopia, ed. G. M. Logan and trans. R. M.Ad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ed. Mary Dewa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Francis Bacon et al., New Atlantis and The Great Instauration,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6;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s. Richard Flathman and David Johnson, New York: Norton, 1997.
[19]有关都铎时代文学与国家主义及宗教改革的关系,详见Philip Schwyzer,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omas Betteridg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有关都铎和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政治结构,详见Paul Cavill et al., ed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Parliament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8; Diarmaid MacCullouch, The Later Reformation in England, 1547-160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20]蒂利亚德的许多用语和概念在今天都老旧不堪,他因研究莎翁历史剧而写成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 World Picture, 1942),试图论证英格兰十七世纪话语如何将人文现象、自然现象和超自然现象相互关联而构筑起一个世界体系和价值结构。相较于福柯《词与物》出版以来学界对于早期现代欧洲文化的研究,蒂利亚德的认识显得单薄、苍白。但在莎士比亚研究内部,针对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各种历史现象之间关系的追踪和厘清仍在继续,格林布拉特的几部作品以及在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不少工作,都尝试从文学内外各因素间寻找对话可能。对本文而言,蒂利亚德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一书中将《理查三世》结尾处里士满的演说置于伊丽莎白晚期宗教和政治紧张场域的洞见,仍然持续地为从当代西方戏剧学和政治学理论出发重新解读此剧提供了支持。
[21]英格兰在内战期间(1649—1653)一度更名为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有关当时共同体国家逻辑的民粹倾向即共和主义(Republican)表述,详见弥尔顿于1649年所作《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see John Milton, 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 Victoria: Leopold Classic Library, 2016)。有关弥尔顿与共和主义的关系,详见David Armitage et al., eds., Milton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关民粹化共和主义政治如何在英格兰内战后部分恢复革命前的政治秩序,详见Sean Kelsy, Inventing a Republic: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English Commonwealth, 1649-165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2]See L. Joseph Herbert, “The Reward of a King: Machiavelli, Aquinas, and Shakespeare’s Richard III”,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44.4 (2015), p.239.
[23]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其思想成熟以及传播均在理查于1485年卒后,因此该剧的舞台人物刻画显然套用了当时的都铎主流话语,与历史上理查是否真受马基雅维利影响无关。关于马基雅维利在早期现代英格兰的影响,详见Alessandro Arienzo, Machiavellian Encounters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iterary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Resto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24]See L.Joseph Herbert, “The Reward of a King: Machiavelli, Aquinas, and Shakespeare’s Richard III”, i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44.4 (2015), pp.238-246.
[25]有关伊丽莎白女王与当时欧洲其他君主的复杂关系,详见Rayne Allinson, A Monarchy of Letters: Royal Correspondence and English Diplomacy in the Reign of Elizabeth I,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有关都铎时代天主教徒在新教国家中的处境,详见Ethan Shagan, Catholics and the “Protestant Nation”: Religious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8页。译文稍有改动。斯金纳认为洛克此作完成于1688年光荣革命爆发之前(see Humanism: 322-323)。
[27]有关《理查三世》为莎士比亚不成熟作品的观点,详见Harold Bloom, 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8, pp.64-76;有关莎士比亚是隐匿的天主教徒的观点,详见Clare Asquith, Shadowplay: The Hidden Beliefs and Coded Politic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28]Elizabeth I, “Address to the Troops at Tilbury (1588)”,in Arthur F. Kinney, ed.,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England: Sources and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1, p.99.
[29]坎特罗维茨认为,国家作为虚构个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意大利罗马法学家乌尔鲍迪斯的鲍迪斯(Baldus de Ulbaldis)的主张,鲍迪斯认为,就国家权力不能间断而言,除真实王冠外,还存在老王死后、新王在加冕之前就已戴上的虚拟王冠,即所谓“不死王冠”(Corona non moritur)(see King’s:336-383)。斯金纳则明言霍布斯受到了前人影响,并勾勒了霍布斯国家理论的历史语境(see Humanism: 341-383)。
[30]有关从二十世纪前期角度针对人格国家概念的讨论,详见David Ranciman, Pluralism and the Personalit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See Max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Heidelberg: Mohr Siebeck, 1994.
[32]有关洛克与霍布斯在统治权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特别是洛克的“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者同意”这一观点和霍布斯关于“被统治者将权力让渡给统治者,但与统治者并无契约关系”这一立场之间的差别,详见Shannon Hoff, “Locke 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77 (2015), pp.1-22;有关两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的不同,详见Jacob Donald Chatterjee, “Between Hobbes and Locke: John Humfrey, Nonconformity, and Restoration Theori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in Locke Studies,19 (2019), pp。2-33。
[33]关于洛克对财产生成过程的讨论,详见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7-32页。
[34]关于韦伯对财富增加与个人伦理关系的讨论,详见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Ditzingen: Reclam Philipp, 2017。
[35]“国王即活着的法”这一思想在中世纪后期和早期现代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see King’s: 87-192)。
[36]Joseph Roach, I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7, p.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7]“contrapposto”一词的字面义也有同时朝相反方向扭转之意,故可传递上文所言强大与虚弱等气质之间的对立。
[38]当时演出此剧时不用马匹,因此角色的舞台表现本身也具有某种原始限定和张力。斯帕西老维克剧团的表演,如舞台倾斜以及借助医疗支架将此躯体的扭曲明白地表现在观众面前,未必是从战马之喻中得到灵感,但也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这种张力。有关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舞台的讨论,详见C. K. Chambers, The Elizabeth S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9]在中世纪战场语境中,“unhorsed knight”(落马骑士)或“unhorsed king”(落马国王)带有明显的失败含义。
[40] Frank Kermode, The Age of Shakespea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62.
[41]女王偏爱戏剧也有其重要的政治目的,她曾说:“我等王者都站在舞台上受整个世界的瞻仰。”(qtd. in Frank Kermode, The Age of Shakespeare, p.63)
[42]Letter from the Lord Mayor of London and the Aldermen to the Privy Council Concerning Plays (1597), in Arthur F. Kinney, ed.,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England: Sources and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1, p.652.
[43]Qtd. in 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a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21. 有关沃尔辛厄姆爵士和英国现代情侦系统的建立,详见John Cooper, The Queen’s Agent: Sir Francis Walsingham and the Rise of Espionag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3; Stephen Budiansky, Her Majesty’s Spymaster: Elizabeth I, Sir Francis Walsingham,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Espiona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此处贬低《旧约》的摩西,抬高数学家、无神论者哈里茨(Thomas Harriot),就是变相在说马娄不信神。
[44]See Walter Benjamin,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Berlin: Suhrkamp, 2000; Carl Schimitt, Hamlet oder Hekuba: Der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 Stuttgart: Klett-Cotta Verlag, 2017.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中,本雅明此作特别针对黑格尔辩证法及它在卢卡奇著作中的体现。从本雅明的立场看,卢卡奇的经典文学论述不但从古代史诗直接进入近现代小说,完全无视欧洲中世纪文化,且在对历史内在与外在特征的阐释上也犯了浪漫主义合形式与内容为一体的象征主义错误;“寓言”(die Allegorie)的作用恰恰是保留或者说凸显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距离甚至矛盾。关于施米特从右翼思想对黑格尔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批评,详见Carl Schmitt, Politische Romantik,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19.
[45]有关寓言在莎剧中的呈现,详见Bernard Spivack, Shakespeare and the Allegory of Evil: The History of a Metaphor in Relation to His Major Villai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Francis Fergusson, Trope and Allegory: Themes Common to Dante and Shakespea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77;Jane Brown, The Persistence of Allegory: Drama and Neoclassicism from Shakespeare to Wagn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6。有关中世纪英国道德剧,蒂利亚德略有提及,但语焉未详(see Shakespeare’s: 92-93),目前较为充分的讨论,详见Julie Paulson, Theater of the World: Selfhood in the English Morality Play,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9。
[46]See Mario Biagioli, Galileo, Courtier: 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of Absolut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see also Mario Biagioli, “Tacit Knowledge, Courtliness, and the Scientist’s Body”, in Susan Leigh Foster, ed., Choreographing Histo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69-81. 有关文化能力的经典讨论,详见Thoma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Verso, 2010.
[47]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167.
[48]See Richard Schechner, Performance Theory, p.167.
[49]See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232, p.298, n.13. 关于格林布拉特后续有关《理查三世》的论述,详见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Stephen Greenblatt, Tyrant,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2018.
[50]See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p.5.
[51]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p.9.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