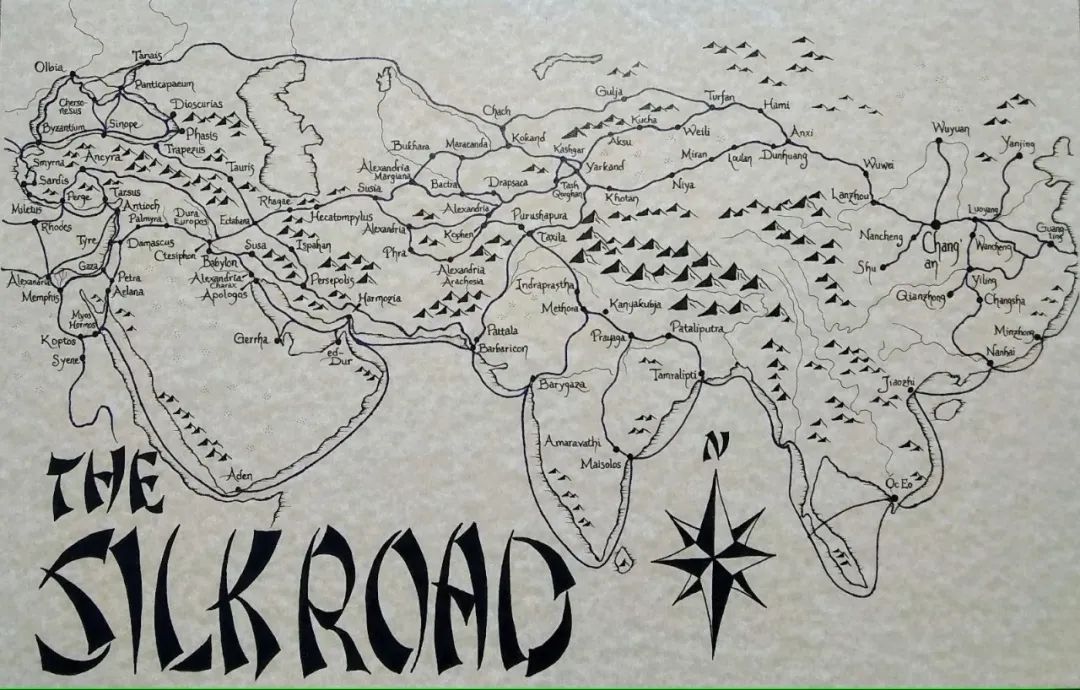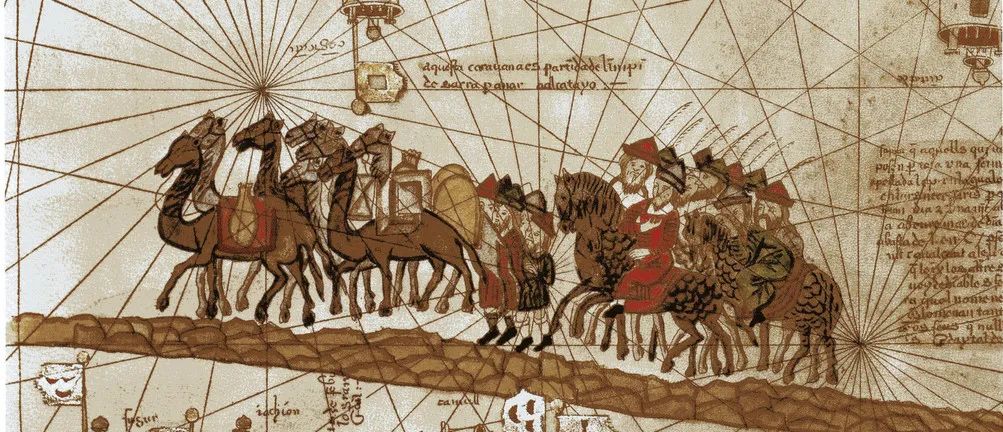编者后记 |《外国文学评论》2024年第1期
从“西学东渐”到“文明互鉴”
埃里泽·拉克吕(Élisée Reclus)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颇负盛名的地理学家,也是“社会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人物,但是他更加引入瞩目的身份则是活跃在世纪末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他参加过马克思亲自创立的第一国际,是巴黎公社的战士,也是巴枯宁在瑞士汝拉山区创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组织——汝拉同盟的成员。因为积极从事反政府的政治活动,拉克吕在青年时代曾经屡次遭受流亡,其行迹遍布欧洲大陆和英国,并短暂地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而且还打算在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古巴和巴拿马定居,从事香蕉、咖啡和甘蔗的种植和经营工作。如此丰富的游历造就了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但是,对他而言,地理学并非一门单纯的自然科学,他坚持要将人文因素纳入到地理学的进程当中,这些因素自然包括了一种能够考量诸多社会和国际力量关系的视角。
尽管拉克吕一生从未来到过中国,但他却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 1902年和他的弟弟翁内希姆·拉克吕合作撰写了一部七百余页的皇皇巨著《中国》,其全名曰《中央之国:中国的气候、土壤和种族》。在该书的首页,作者开宗明义地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欧洲和中国、(远)东方和西方发生激烈冲突之际,我们期待着正义和宽容到来的时刻,到那时,双方可以展开和平的交往,彼此不再是狼与狼的关系。接着,作者分别援引同时代法国两位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的话说,中国理应与欧洲各自分享人类历史的一半篇幅,若说现代欧洲诸多民族是继承周围多边的历史而来,那么中国的传统却是一脉相传,而深刻的创造性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秘密。因此,拉克吕认为恰恰要在这个中西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的紧张时刻,本着“真诚”和“同情”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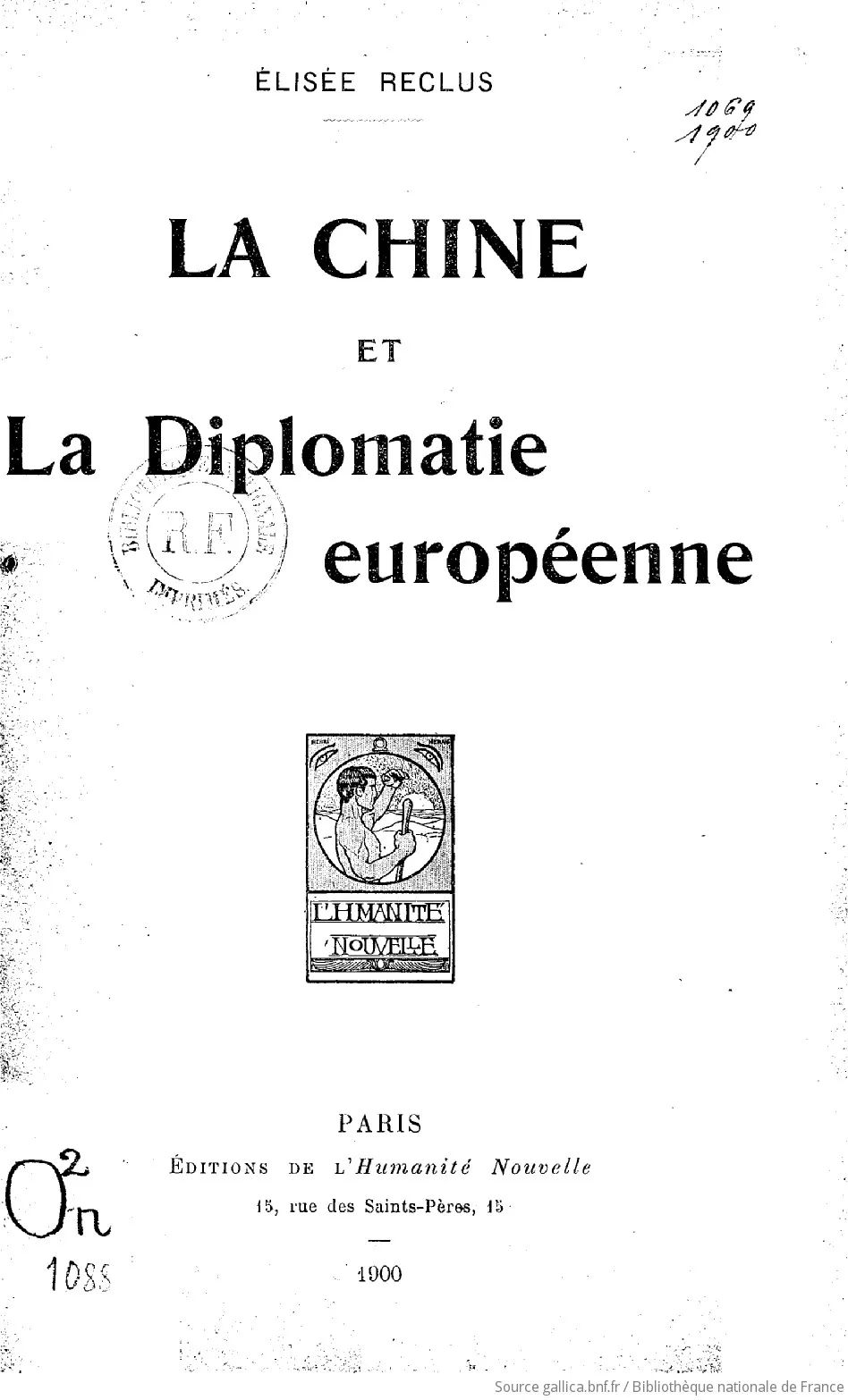
拉克吕《中国与欧洲外交》(1900)扉页
那么,这位地缘政治家是如何看待世纪之交发生的东西方冲突,或者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冲突的?与同时代那些依然沉迷于殖民主义梦想的欧洲知识分子们不同,拉克吕首先认为彼时处于内外交困当中、积弱已久的中国之所以国脉尚存,乃是沙皇俄国强大的殖民力量与欧洲人的“妒忌”和“野心”之间相互抗衡的结果,换言之,是欧洲列强相互妥协的结果。他告诫欧洲(包括俄罗斯)人不应当指望能够肢解中国,“中国长久以来或者说永远都不可能被挤压,即便是她在将来的某日或对或错地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在牺牲掉了其语言文字的相对稳定性的情形之下也会依然如此。”拉克吕进而预言,“无论中国和日本在面对欧洲列强时的政治命运和军事命运如何,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东西方各民族的命运自此之后将越来越会休戚相关,而且随着双方关系的日益密切而更是如此,这如同是滚雪球一般,由一片雪花的下落渐成参天之势。”尽管庚子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加剧了中欧国家间的敌意,但频繁的贸易流通和人员往来却使两种不同的文明相互渗透,“加农炮未能完成之事,自由交往却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完成了。”贸易和人员的往来往往与思想的交流相伴,东西方文明于是均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世界越来越小,各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已经不能被隔离在特殊的地域内部独立发展,而是混合成为一种更为高级的文明”。针对当时华工不断涌入欧美国家与当地工人产生冲突,甚至于排华事件频仍的情况,拉克吕并不认为来自产业领域的“战争”会持续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相反,黄种人代替白种人进入工厂工作能够拉低平均工资水平,并在世界范围内达成一种普遍的收入平衡,直至一种新秩序出现。拉克吕说:“这种平衡迟早都会形成,人类将会适应整个星球的共同财富所赋予他们的新的命运,相反,冲突时期的灾难将会随时发生……欧洲、美洲和东亚的文明世界将趋于平等。”就其结果而言,借助于交换、教育和人员往来,不同文明之间的联合将越来越紧密,而它最终会部分地弱化文明之间的差异。

八国联军与清兵对阵插图
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外表上,同时也呈现为不断变化的倾向和思想。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学习西方的能力,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由此推测日本尚且如此,作为其文化母国的中国必然也会猛然苏醒并且浴火重生,从而对欧洲文明构成巨大威胁。与 90年后美国政治理论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在拉克吕看来,中欧文明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威胁,二者相接触的结果也并非为了抬高一个压倒另一个,否则人类将会抛弃现代文明的成就,重蹈黑暗的中世纪。而中欧两种不同文明的接触、影响和相互学习必将给双方带来深刻的变化。当欧洲人面临与中国文明的竞争之际,他奉劝欧洲人不应为了避免遭受失败而逃离战场,不应故步自封,重新封闭中国的港口,从而将中国推回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古老的状态和愚昧当中,因为“东亚自此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的组成部分”。拉克吕问道:“在普遍的历史运动中,与五亿(东亚)人的接触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重视对亚洲东方和黄种民族的学习,对未来的文明而言,这是有用的甚或是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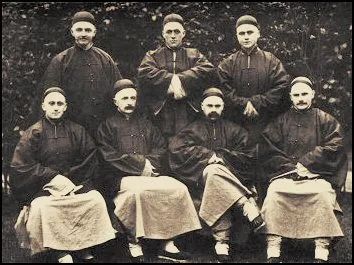
晚清在华传教士
中国人对西方语言和文明的接触和学习始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以及晚明士人们对西学和西方技艺的摄取。十九世纪中期,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各式各样的教会学校,开始纷纷教授以英文为主的外文知识。1862年清廷为了办理日益繁多的外国事务而设立的同文馆是中国人系统学习和翻译西方经典和西方文明的标志。1902年,也就是在拉克吕发表前述《中央之国》的同一年,在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外国语言文字学”才作为七科之学其一的文学科门类之一首次出现。在该章程中,文学科注重中外兼蓄,文、史、地并存,在中国文学门之外,设有英、法、俄、德、日等国文学。在民国政府 1913年颁布的《大学规程》中,文学门中除了国文学之外,还包括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等八个学科类别。这个规程在外国学习之外,特别强调国别史和文学史的兼修。
人们通常说,我国的外文学科是百年来西学东渐的结果,而西学东渐则是晚清政府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被迫做出的举措。西学东渐分别在晚明、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前后多次引发过中国传统的危机,中西之争一直延伸到 1920和 1930年代的东西文化论战,直至今天。中国人对西方知识和文明的学习先后经历了以儒学吸纳西学、西学自立、以西学阐释传统和再造新文明的过程,正如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1921)一书中称东西方文化面临着相互转化的趋势一样,在他看来,未来的世界文化将经过三个时期,即西洋化、中国化复兴和印度化复兴。同样地,拉克吕也认为,学习异域文明是一个文明赢得生存的需要,诸文明之间出于生存之需发生的相互影响和变化是文明自身发展的特性。他断言,如果清政府没有遭到太平天国运动和伊斯兰起义的干扰,那么中国人向西方文明学习则必然呈自觉之势。
在我们当今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外文学科也走到了自身发展的十字路口。回顾百年以来中国外文学科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外文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新兴学科、跨学科名目层出不穷,外语教学、语言学、翻译学、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区域国别学等等不一而足,现代性、后现代理论、形式批评、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批评等方法论如鲫过江,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外文学科的特质、宗旨和使命究竟是什么?摆脱了工具论之后,外文学科是要重新回到(古典)语文学,还是趋之若鹜地走向区域研究?不要忘了,中国的外文学科本是应我们民族学习西方文明,并在列强环伺之下求得生存的需要而起,以翻译、研究、反思、批判和汲取西方文明的养料为己任,肩负着再造中国现代文明和重塑新的文明主体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