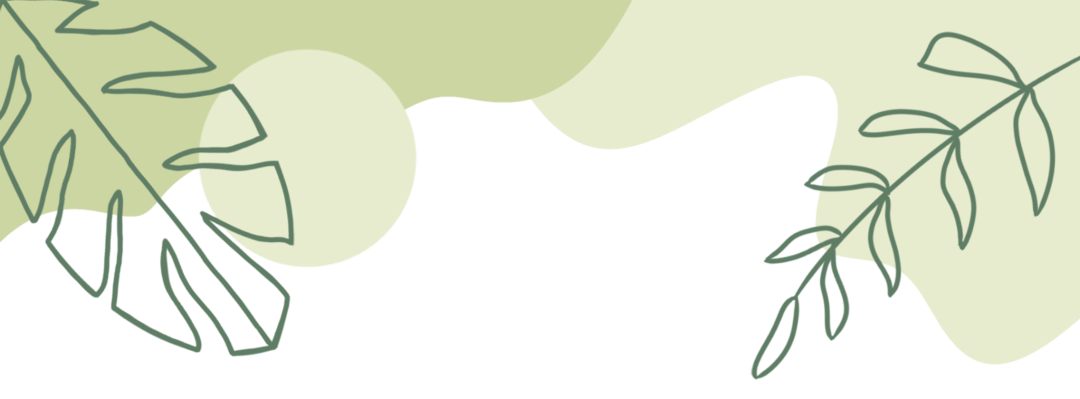编者后记 | 《外国文学评论》2025年第3期
2025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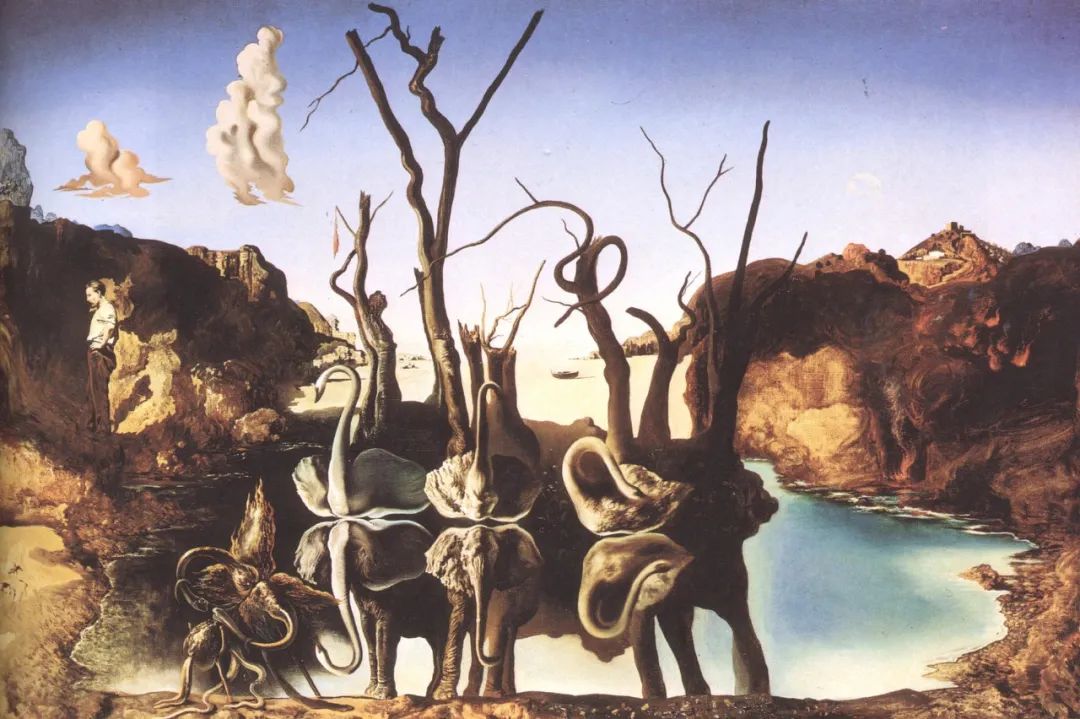
《天鹅映象》(萨尔瓦多·达利,1937)
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那些纵横捭阖的著作,有“当头棒喝”经历者,不在少数。不过,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詹姆逊,他迎面一句“ What’s your field?”(“你的领域是什么? ”),却让我始料未及,竟无言以对。一个本可张口就说出答案的简单问题,我却犯难了,并从此在心头萦绕不去。难道我学了一点西方文学理论皮毛,读了一两部简版的英美文学史,外加一点莎士比亚、简·奥斯丁、爱默生、霍桑、勃朗特姐妹、马修·阿诺德、吉卜林、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等人的作品,就敢妄称已进入一个名为“英美文学”的“领域”,与詹姆逊碰巧是“同行”,而“同行者”中还有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爱德华·萨义德等人?
多年后,我对詹姆逊的那个问题似有所悟:以跨学科的总体性为批评追求的詹姆逊,无论他侵入其他学科多远,总是不断重返他的“根据地”——他的“领域”。他的那个“根据地”,早被他像考古学家那样一厘米一厘米丈量过,挖掘过,说他是该“领域”的顶级“专家”也不为过,只不过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底色使他不以某个“领域”的“专家”自限而已(如果他以“内外”画地为牢,则与勒内·韦勒克为同道),但恰恰又是他的“根据地”为他的“越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基础力量。
相同的经历,也发生在多年前我参观达利画展的时刻,只要眼睛靠近画布,就会发现达利常常在画布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个“古典”风格的微型素描。这位在画布上天马行空的创新家,其实受过极为严格的绘画基础训练。扎实的“基本”训练,才是他天马行空的创新的基础。
回到三十多年前詹姆逊对我的“当头棒喝”:“你的领域是什么?”至今,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尽管每年年底在向单位提交的考核表的“专业”一栏,我常常诚惶诚恐地填上“英美文学”。如果我多一点自信,我或许可以填上“外国文学爱好者”。
在类似于“社论”的《编后记》中掺入主编个人经历,当然欠妥,但这些个人经历所涉及的问题,却与外国文学学科当今的状况息息相关。当今,或许没有哪一个学科,像外国文学学科那样,在自身的式微中经历着“跨学科”的亢奋,以致给人一个同等亢奋的印象,即当今时代之于外国文学学科,是一个迫切需要大师而不料大师竟鱼贯而出的时代。不过,正如“外语 +”、“复合型人才”这些听上去仿佛是进攻而实际上是撤退的号令所暗示的那样,以弱化自己的“领域”或者说“根据地”来亢奋地追求“跨学科”,除了获得外行的嵩岳三呼和内行的笑而不语,对外国文学以及它发誓要去“入侵”的那些学科,都将是一场名誉损害。
“领域”,类似于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自己无“领域”,就谈不上对其他“领域”的“入侵”。所谓“入侵”,一定是“领域”对“领域”的入侵。外国文学学科的式微(假定它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曾一度繁荣),源自一种自我抛弃,不把自己作为一个学科,一块“领地”,日兮夜兮,耕作不息。
“专家”的身份近来颇遭物议,不是因为“专家”太专精,以致让普通读者自感匮乏(此时,对专家,他们会肃然起敬,因为他们在知识上有所获),恰恰相反,是“专家”游谈无根,信口开河,没有显示出本该与“专家”身份配套的“专业性”。本刊一直大力提倡“跨学科”,但基于一个前提,即先做到在“本学科”(外国文学)的深厚扎实,而且,越是深厚扎实,就越有“跨学科”的本钱,舍此,则“本学科”与“跨学科”偕亡。为“跨出去”,必先巩固自己的“根据地”。或许,外国文学工作者应该常常自问一句:“我的领域是什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