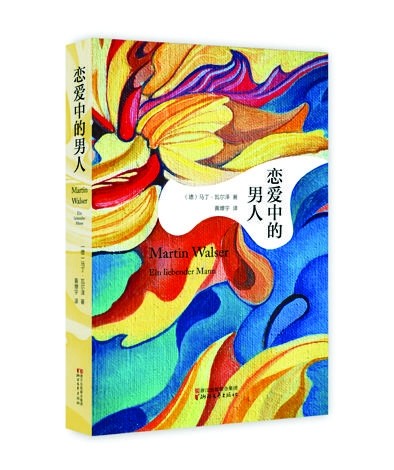
《恋爱中的男人》[德]马丁·瓦尔泽著黄燎宇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恋爱中的男人》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描写了他的一段黄昏之恋。歌德七十三岁时在疗养胜地马林巴德度假,因参加玛利亚温泉城的假面异装舞会,而对芳龄十九的少女乌尔莉克一见倾心。此译本并非瓦尔泽新作,但当最新再版的书摆在面前,空气中隐约散发出丝丝特有的油墨书香时,瓦尔泽的喜悦显而易见。用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的话说,“老爷子眼泛泪光,签名的笔尖微微发颤”。该书已陆续被译成十九种语言。
提及德国战后文学史,马丁·瓦尔泽必不可缺,正如北京大学德语系黄燎宇教授所说——“瓦尔泽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并不意味着他比同为四七社成员的君特·格拉斯以及海因里希·伯尔缺少艺术才华。更重要的是,瓦尔泽是惟一在有生之年享受到其他德国作家只能在死后才可以享受到的待遇的作家。”瓦尔泽个性独特,敢说更敢干,一生话题不断,尤其在反对越战、主张两德统一、反对奥斯维辛等诸多敏感问题上,简直就是“德意志的小钢炮”。他的文字常饱受争议,但即使是引发大规模批判,只要作品一经出版,人们照旧蜂拥购买,欲罢不能。
《恋爱中的男人》取材真人真事,作者用充满理解与同情的笔调,刻画出老男人与小萝莉之间的感情,爱恋交杂着嫉妒,男女情感于信赖与疑虑中纠结。欢乐即痛苦。外人眼中的不齿“忘年恋”,在瓦尔泽的笔下始终贯穿着希望,阅读获得新的体验,并深陷其中难以自拔。瓦尔泽准确勾勒出“英雄暮年,春心重发”的心理状态——“他一个钟头要从写字台边跳起来五次,他跑到窗前,希望乌尔莉克马上就出现在对面的露台向他挥手,他也挥手……”瓦尔泽接受采访时说到自己,“创作本书时我始终激动难耐,三个多月就完成了它,我的书桌对我的写作作出反应,我写得太激动,桌子都会震颤……”他想表达出一种本我的生命体验。
趁着马丁·瓦尔泽来上海举办新作阅读对谈活动的机会,我去目睹了老先生的风采。已是鲐背之年的瓦尔泽表情丰富,精力充沛,座谈会上他偶尔会顽皮地噘嘴吐舌,眼珠左右转个不停。台下有人小声议论,说本书主人公歌德,其实正是作者自己本人。瓦尔泽笑起来,他说:“乌托邦才是小说的立身之本,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小说中每个人物的喜怒哀乐,正如《恋爱中的男人》,本意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对歌德进行温柔的批判……我刻意让歌德获得单相思体验,因为他自信发现了世上一切悲剧的起源与罪魁祸首。爬上海拔二千二百四十四米的西奈山,摩西气喘吁吁,最后并没听见真正的第一诫——‘你不可以爱’——歌德为此感叹道——‘如果摩西从西奈山带回这第一诫,除了悲剧,人类不会有任何欠缺。爱情是一切悲剧的起源。’关于这本书,我要说的是,我只写自己匮乏的东西,换句话来说,所有让我有创作欲望的东西,都是我的缪斯,也就是‘匮乏’。”
瓦尔泽在会上朗诵他即将出版中译本的新作——《寻死的男人》选段。我虽不懂德语,却被老爷子的激情澎湃彻底感染。瓦尔泽的诵读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不时要加以手势,气氛愈发热烈。读到某处他忽然一巴掌拍在讲桌上,有时眼睛眯起,身体微微摇晃,甚至走到主席台中间来回踱步,把阅读会延伸为一种“审美愉悦体验”。瓦尔泽非常厚爱本书中文版本的译者,他称呼黄燎宇先生为“影子制造者”——《恋爱中的男人》中一位女诗人恰好就把译文比作原创文字的“影子”。黄燎宇笑着告诉听众,瓦尔泽在德国公众中的影响,仅次于德籍教宗本笃十六世。然后他向瓦尔泽抛了一个问题:从文学史来看,爱情似乎一直是以年轻爱情为主流,老年人的爱情凤毛麟角,而《恋爱中的男人》和即将出版的《寻死的男人》,都是描写老男人,那你是否有意要向这个被年轻爱情主宰的世界发起挑战呢?瓦尔泽深呼吸一口,他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写老少恋,男的比女的大二三十岁,女性主义者立马跳出来骂,骂我是老色鬼。那我写歌德,歌德比这个女孩大五十还多,不仅没人再骂,还一再夸赞。”
在中国,格拉斯拥有大量的普通读者,资深文学爱好者则喜欢阅读伯尔,“瓦尔泽”似乎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但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我似乎更喜欢瓦尔泽。我觉得瓦尔泽属于那种走出作品也不乏智慧与诗意的作家,诙谐幽默且谈吐非凡。要说文学史上古稀之年还在描写爱情的作家并不鲜见,七十几岁的马尔克斯写出《苦妓回忆录》,老年的川端康成写下《睡美人》,而这一次,我们听年近九旬的瓦尔泽聊聊他心中的爱情——“如果一个女人不是你想象中的模样,你的生活就是幻觉,你还对这幻觉无能为力,这便是‘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