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中国缘”
作者:
来源: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裸体的玛哈》英文版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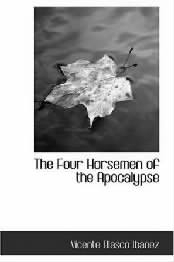
《四骑士启示录》英文版书影

《五月花》英文版书影
编者按:北京大学西语系博士生导师段若川教授已经去世十年了。她生前曾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和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数十年如一日,勤奋,严谨,持之以恒,成果颇丰,深受学界同行的好评,尤其受到弟子们的尊敬和爱戴。本刊特刊发她的遗作,以志纪念。
一
早在20世纪初,中国人民就熟悉西班牙著名作家维生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ez,1867-1928)的名字了。他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与国外,特别是与西班牙的文化交流的大力展开,他有近十部小说在中国出版。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出生于巴伦西亚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早年时家境并不太好。年轻的布拉斯科觉得自己受到家庭的约束,就积极参加种种社会活动,尤其表现出对政治和文学的兴趣。从思想倾向来看,他和与他年龄相仿的西班牙“98年代”作家乌纳姆诺和巴列-因克兰等人的感情息息相通,他们一道从事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可以把他们都看作是19世纪末站在西班牙人民一边、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一群进步作家。
年轻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曾在巴伦西亚大学学习法律,但是他中途辍学,来到马德里从事文学。他曾给一位名叫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冈萨莱斯的作家当过秘书,熟悉了工作以后,他可以整章整章地替这个作家写作,并以那人的名义发表。同时他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最早的一些作品多是反映巴伦西亚地区人民生活的小说。
在马德里时,他更热衷的活动是政治,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鼓动家,他毫不留情地抨击反动的教会势力和政治寡头。因此,他也不断地受到当局的迫害,1890年曾被迫流亡法国。从法国回到巴伦西亚后,他与堂妹玛利亚·布拉斯科结婚,生有四个子女。1894年,他拿出自己的全部资产,创办了《人民报》,这是一份为最底层的人民说话的报纸,因此引发官司,他被迫流亡到意大利。由于积极支持1895年古巴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他曾被官方逮捕。但是由于他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被选为巴伦西亚议员,而议员是享有政治上的豁免权的,于是,当局不得不将他释放。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即便在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中、不断地被逮捕或被迫流亡国外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此间他发表的作品有旅行纪实《巴黎,一个入境者的印象》(1893)、《在艺术的国度》(1896),小说《稻子与双轮篷车》(1894)、《五月花》(1895)、《茅屋》(1898)。他到君士坦丁堡旅行的结果是写出了一本书,题为《东方》(1907)。
他仍然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直到1907年,他已经是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选为议员。从1907年起,他进行了一次长期的长途旅行,飘扬过海来到了阿根廷。好像是为了在那里实现他在西班牙难以实现的政治理想似的,他在阿根廷创建了两座垦殖地,给它们起了浪漫又思乡的名字,一座叫“塞万提斯”,另一座叫“新巴伦西亚”。但是,他大概只会写小说,而不善于经营农场,他失败了。而他在阿根廷期间曾在很多地方作讲座,却获得了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回到了欧洲,站在同盟国的立场,反对罪恶的战争。与此同时,由于他的作品积极向上的思想性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在获得声誉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他的作品被美国电影界搬上银幕,旗开得胜。1921年,他搬到一个名叫“蓝色海岸”的地方定居。1925年,他妻子去世,不久后他与一位智利女子爱伦娜·奥尔杜萨尔·布尔内斯结婚。1928年,他来到离西班牙不远的一个法国小镇芒东,在那里度过了他光辉一生的最后的日子。后来,有人在他位于芒东的故居开了一家酒店,那里成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故居博物馆,笔者有幸结识了酒店里那一对热情的老板夫妇,他们每次都到西班牙巴伦西亚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关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学术研讨会。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生中著作颇丰,有四十多部出版物。他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报刊文章、文学评论或随笔,有戏剧,还有小说。他的小说是诸多作品中最突出的,尤其是他的巴伦西亚时期小说,都非常优秀。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杰出的短篇小说。这一切使他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西班牙现代文学之林。他的这些作品充满活力,富有创造性,对细节的描写准确、鲜明、生动。有人把这种写法归纳为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说他善于营造一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充分地表现了人际的紧张关系,也就是巴伦西亚地区的地主与雇农之间的冲突。
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橙林间》(1900)、《芦苇与泥淖》(1902)、《大教堂》(1903)、《闯入者》(1904)、《游牧部落》(1904)以及《血与沙》(1908)等。还有如《妓女松尼卡》(1901),是一部历史小说,写的是罗马帝国的故事;小说《裸体的玛哈》(1906),其风格近似于邓南遮的作品,带有现代小说偏向于虚构的成分。虽然仍带有自然主义特色,但是这些作品表明作者的创作面已经得到了拓展,风格也丰富多变。有人认为这种自然主义带有政治倾向,受到处于激情状态中的左拉风格的影响。
然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是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四骑士启示录》(1916)。这是一部发聋振聩的反对世界大战的激越的呼声。之后的作品有《我们的海》(1918)等等。
1923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环绕地球的旅行,为期半年,旅行的结果是写了《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1924-1925),这是一部三卷本的游记。
布拉斯科最后几年写了一些历史小说,这些作品都突出了西班牙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如《海上教皇》(是写圣本笃十三世的,于1925年出版)、《寻觅大可汗》(是写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的,于1929年出版)、《圣母的骑士》(是写阿隆索·奥赫达的,1929年出版),还有《揭下面具的阿尔丰索十三世》(1924)是描写流亡的爱国者们与独裁者普里莫·里维拉和反动王朝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二
对于遥远而神秘的中国,布拉斯科情有独钟。在他那三卷本《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的第二卷中,我们看到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再次说服自己,我正在北京,但是这也阻挡不了第二天我产生同样的疑问。住在这个城市是多么不平凡。它的名字我们小时候就学会了,那是一个我们永远也看不到的极其遥远的地方。
这个中国的城市在我们脑子里最初的印象是远得没法说的、从没那么远的地方。小时候有人说某人要永远地离开了,就说:“他要到北京去了”,就不用再做什么说明了。有的人为了强调某种事物永远不可能实现,或者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就会说:“这儿不成,就是到北京也不成。”这就把一切都说明了。
布拉斯科是用这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北京是多么遥远,多么神秘!但是,在20世纪初,1923年,他终于乘大客轮漂洋过海,从美洲取道日本和朝鲜,乘火车从中朝边界入境,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啊!
当时朝鲜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实际上,他们已经从各个方面控制了东北地区,而盘踞在东北的军阀们也在变本加厉地鱼肉百姓。于是,我们的作家对中国的头一个印象,来自于在一座火车站看到的情景:
我们看到车窗底下,上百个孩子,他们的身体被铁丝网上的刺扎着,却没有感觉……大家都伸着胳臂拥挤着,手掌张得开开的。他们叫喊着,哀求着,还有几个哭泣着。最小的几个翻滚在地上,被同伙们踩着,但是他们立刻站了起来,继续参加到乞讨的合唱中。
列车员叫我们不要给在车站上乞讨的人群施舍,中华民国要消灭这种往昔的劣习。但是怎么能拒绝这持续了好几分钟的恳求的声音呢。孩子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尤其看到的是带有异国情调的孩子,就更吸引人了。这一大群雪崩似的孩子,他们满脸皱纹,眼睛就像老头子的似的,还有打扮和表情都像成年妇女似的圆脸女孩,这促使我们没有听列车员的话,开始将成把的硬币从小窗口扔出去。
还不如不这样做呢……!一看到钱,大人就涌到孩子们那里。冷漠地看着火车远去的大小伙子们,扑到小孩子身上,拳打脚踢扇耳光,去抢他们的钱。
从上述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的作家是怎样地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并且为他们担忧啊!然而这些并不是我们的作家看到的唯一的东西。在沈阳,他看到清朝最早的几个皇帝的宫殿和陵墓,他被那些宏伟壮丽的建筑物震惊了。当他看到了北京的故宫、北海、颐和园以及长城等气势恢弘的历史古迹时,他更被东方文化陶醉了。他望着“真龙天子”的红墙黄瓦,天坛里与数字“九”紧密相关的洁白的寰丘,琢磨着中国人心中的天、地、人的玄妙东方哲理。他喜欢北京的四合院,但是他看不惯以人代马的人力车,也不喜欢被中国人称为“三寸金莲”、而被他的同胞作家皮奥·巴罗哈称为“羊蹄子”的封建残余。中华民国建立了,可是末代皇帝和他的皇后、妃子们,还有他们的太监们仍然怀着复辟的梦想,盘踞在故宫的一隅,接受着遗老遗少们的顶礼膜拜。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从北京的空气里闻出了一股陈腐的味道,于是他到了上海。他发现那里的空气比北京的要活跃得多、愉快得多,那里有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他们开创的民族产业。
他们一行从上海乘坐豪华游轮“福兰科尼亚”号前往香港。在香港他领略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香港工人曾举行罢工,使香港变成了“臭港”。而离香港不远的广州,孙中山先生正在准备北伐,共产党不但积极参加北伐,而且还组织起民众,把工人、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命气势风起云涌,一向支持民众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怎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怎能不就近去目睹中国的革命呢?他想从香港到广州去看一看。他的旅伴们劝他不要去,因为这些工人农民肯定会仇恨一个白人的。但是他决心已定,旅伴们以生离死别的心情与他告别。可是他安然无恙地、心满意足地回到了游轮上。
在另一个篇章里,他以激动的心情描绘了他一天早晨看到的奇观:
到香港的前一天,我目睹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场面。我们正航行在台湾与内地海岸之间的海上,离一个在西班牙语里称作“钓鱼岛”的地方不远,那个海湾里经常波涛汹涌,即便天气很好也如此,这对小船很有威胁。太阳刚刚出来不久,我发现福兰科尼亚号上的几个水手互相招呼着,他们跑到轮船的一侧。我必须凝聚全部视力,好不容易才看到那奇特的情景。三个半裸的中国人站在波涛间,朝我们驶来;波高浪陡,不时把他们埋在波谷,又把他们掀起,时隐时现。只有当他们从我们的轮船旁驶过,或更确切地说,当福兰科尼亚号驶到他们跟前时,我才发现,他们三人的那条船,不如说是一副棺材。那是一条三米长的小船,漂在离船帮只有几厘米的水面上。由于这条船不断地进水,在海面上几乎看都看不见它。他们中的一位时不时地放下桨,从那黑乎乎的船底里把水舀出来。他们就这样在海峡的巨浪中前进。这天早晨,连福兰科尼亚号都被巨浪颠簸得摇摆不定。
在福兰科尼亚号的指挥台上值班的军官微笑着赞扬这些中国人的大胆、坚定。他说,“如果有人懂得怎样指挥,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员。”三个船民从我们的船边驶过,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们,他们很有尊严地、毫不动容地用脊背对着我们。
我认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对这三名中国船民的描写很有象征意义。他很欣赏中国人民的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他们头也不回地、一无反顾地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牢牢记住的那位军官的话,实际上也就是他自己的心里话:只要有人懂得怎样领导,中国人会成为最优秀的海员!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果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布拉斯科地下有灵,他也会含笑九泉的。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一生中对中国的旅行大概就是这一次,总共几十天的工夫,但是在这部游记中,他竟用了近200页的篇幅来描写他看到的中国的各个地方,从东北的沈阳,到北京、上海、香港、广州,一直到澳门。可见中国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短短的几十天中,他看懂了中国,他看懂了中国人的心。他对三个船民的描写就证明了这一点。
三
“投桃报李”,这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用在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身上也很实用。他了解中国人民,他也是中国人民最早地了解和最敬重的一位西班牙现代作家。而且,最早提到他的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他的《华盖集》中,1926年7月的日记里写道:“最近两年我们听说来了四个有名的文人……也有西班牙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早些时候介绍过的。问题是在欧战期间他为人道和世界主义唱赞歌。问题是根据教育部的纲领,他是根本不适宜于中国的。所以谁也不理睬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们是竭力推崇民族主义的。”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好几个信息:首先,早于1926年,中国人已经认识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了,也许已经读到过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了。第二,鲁迅先生已经知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做了些什么,至少已经听说过他写的《四骑士启示录》这样一本书了,并且知道此书在世界文坛上的反响了。第三,由于当时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任职,可是他是站在罢课学生一边,反对军阀政府的,因此,为逃避军阀迫害,那一年他跑到南方谋职。所以谈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他才会说什么“谁也不理睬他”,“根本不适宜于中国”等反话。当鲁迅先生说这些话时,也许他脑子里还在想着牺牲了的刘和珍等烈士流下的鲜血。他曾于1926年4月12日,在《语丝》上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
1928年,鲁迅先生又一次提到了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他同皮奥·巴罗哈都是“西班牙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鲁迅论外国文学》,福建师大中文系编,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1929年鲁迅先生提到皮奥·巴罗哈时又一次提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说前者不如后者知名,是因为后者的小说被美国的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在上海上映,市民是花了钱去看了才知道的。这里指的就是《血与沙》。因此,鲁迅有点为巴罗哈鸣不平,于是,他亲自出马,翻译了巴罗哈的《山民牧唱》。
而正式向中国读者介绍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是戴望舒先生。他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经历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是为正义事业而奋斗,都曾经被捕入狱;他们都才华横溢,他们的心都充满爱和善。所以,戴望舒先生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情有独衷就不难理解了。戴望舒先生解放以前就翻译和发表过这位西班牙人的一些短篇小说。比如,1928年1月23日在《文学周刊》第5期上有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一个悲惨的春天》;1928年1月25日在《未名杂志》第2卷第1册发表他的译作《巫婆的女儿》。
很可惜,戴望舒先生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短篇小说选》于1956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该书是从1922年法国恩奈斯特·福拉马荣出版社的一个法文本翻译过来的,包括《巴伦西亚最后一头狮子》、《巫婆的女儿》、《一个悲惨的春天》、《墙壁》等作品。总之,这是解放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个译本。
此外,从解放以后就有一些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零零星星地发表在我国的报刊上,如《扒车人》(又译为《无票旅客》)、《一枪二鸟》等等。
1958年《血与沙》的汉译本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吕漠野先生从一个世界语译本和一个英语译本译出的。而第一部由原文直接翻译成汉语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长篇小说是《茅屋》,是庄重先生翻译的,于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想当初,《茅屋》在西班牙刚刚问世时,命运并不太好,只印刷了700册,卖出去500册。但是一个法国译者给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了信,要求作者同意他将其翻译成法文。由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太忙,就没有理会。过了一段,这个执着的人又寄来了同样内容的信,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在意。但是忽然有一天,马德里满街的报纸都在说,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小说《茅屋》被翻译成法文,大获成功,受到法国评论界的很高评价。从此,一国跟着一国,争相翻译和出版这部小说,《茅屋》走向了世界。而他当初与老友一道卖掉的那500本书,每个人才分到78个比塞塔,还多亏当时的印刷费便宜!
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血与沙》的命运要比《茅屋》的好得多,《血与沙》自从一问世,就得到读者的青睐,也被各国争相翻译出版。加上它被美国好莱坞改编成电影,借着银幕的翅膀,飞遍了全世界,以至于早在1926年,鲁迅先生就提到这位作家和他的这部作品。《血与沙》是属于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第二创作时期的作品。此时的作家已经把他的写作范围扩大到巴伦西亚以外的地区,使自己的创作题材更加广泛了。据我认识的一位研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专家说,虽然《血与沙》的主要舞台是在塞维利亚,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这个城市逗留的时间却非常有限,但是,他能把塞维利亚的城市风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写得那么准确生动、细致入微,着实令人惊叹。这就像他在《一位小说家的世界旅行》中一样,他在中国才旅行了几十天,就写出了近200页的文字,而且,还稳稳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作家的敏锐的洞察力,当然,也感叹他的那支生花妙笔。
五六十年代,当《血与沙》在中国出版时,在比较“左倾”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囿于当时的认识论水平,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和对人物特征的把握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比如,他们把西班牙的斗牛看作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把它看成纯粹的服务于上层阶级的消遣。其实不然,西班牙斗牛与古罗马时代的人兽之间的格斗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人身安全有了较大的保障,虽然如在任何行业一样,死人的事情总是免不了要发生的,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因噎废食。斗牛用的公牛是西班牙的一种特产,如果没有了斗牛业,这种猛兽恐怕就不会在西班牙存在了。相反,斗牛业的兴旺,促进了西班牙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斗牛,固然是有钱人的消遣,但是每个斗牛场上的一万多名观众不可能全都是有钱人,西班牙喜欢斗牛的人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发展到今天,西班牙已经成了世界三大旅游国之一,它靠的是什么?旖旎的风光、灿烂的太阳、沙滩和海岸、动人心弦的斗牛、撩拨激情的弗拉门戈舞……你能笼统地用“有钱人拿穷人开心”一句话来说明斗牛这一西班牙国粹吗?当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介绍了潘普洛纳的奔牛节以后,每年有多少外国人自愿地从世界各地奔向那里去体验那一份刺激,那一份疯狂,那一份欢乐!你能说那都是资产阶级的无聊消遣吗?
当时对书中的莫拉伊马侯爵的评价也欠公正。书中有很大一段描写他与他饲养的一头名叫“上校”的公牛的感情。由于侯爵的社会地位,中国的评论家就认为他不会有什么真挚感情,他的这种感情只是一种虚伪。这样看问题就把问题简单化、格式化了,把人物脸谱化了。不论是哪个阶级的人,他的性格都具有多重性,每个人物都有多方面的表现。其实,莫拉伊马侯爵是这部作品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他与“上校”之间那种人与兽的沟通,那种情谊,那种心灵感应,正是这部作品中感人至深的部分,起码对于我来说如此。我觉得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也是用了他的全部感情和心灵来写这一段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莫拉伊马侯爵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土财主、牧场主,牲口贩子。他的封号是从他那骁勇善战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他家的领地是祖辈与摩尔人拼死作战的功绩中挣来的。侯爵也从他们那里继承了世界著名的西班牙骑士精神,他们豪爽、慷慨、大度,乐善好施,连对强盗小羽毛都网开一面,采取宽容的态度,给他留下生存空间。他虽然享有爵位封号,但是却没有离开土地,他对于自己喜爱的养牛事业还事必躬亲,对观气象、做农活、看收成、骑烈马、围公牛、轰牛群等劳动者的活计样样在行。夏天,他也会光着膀子与朋友一道喝啤酒,冬天踏雪去狩猎。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更多的是继承了西班牙民族的优良传统,有西班牙人的那种既勇敢又善良的优秀品格,而想不起来把他看成一个伪君子。我觉得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使用了那么多的笔墨来赞赏他的美德之后,并不是为了把他写成一个伪善者。而相反,对于一个来自底层的人,一个真正的劳动人民,加亚尔多的姐夫,那个制鞍匠,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好像从来就没有拿好脸看过他。事到如今,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用老一套来说什么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污蔑劳动人民了吧!
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变万化的,看待一部文学作品也不应简单地、带着框框地去分析。如果我们能懂一点文艺理论,懂一点美学,那样去阅读文学作品固然更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读小说就是为了消遣,我们看到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么动人的故事,又使我们领略了西班牙的如画风光,神奇风情,了解到这么多的斗牛知识,收获也就很不少了。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作者:段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