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火旁——爱尔兰盖尔语民间故事集》:只要爱尔兰语活着,它们就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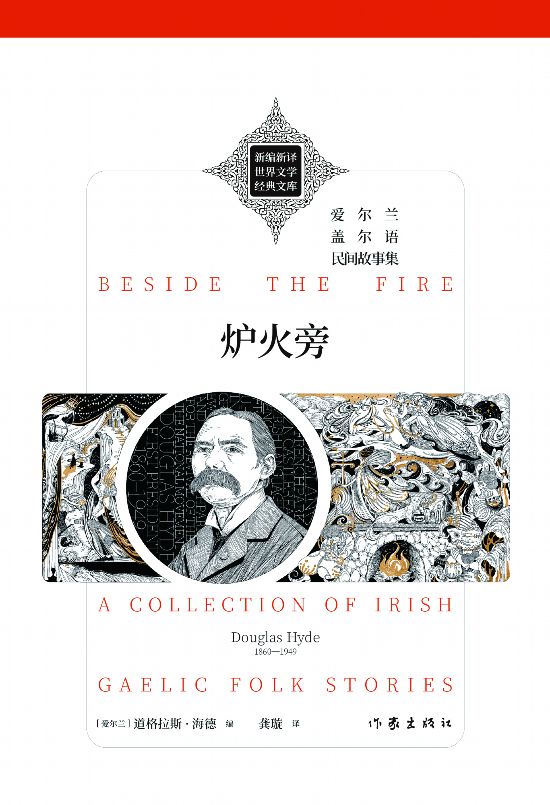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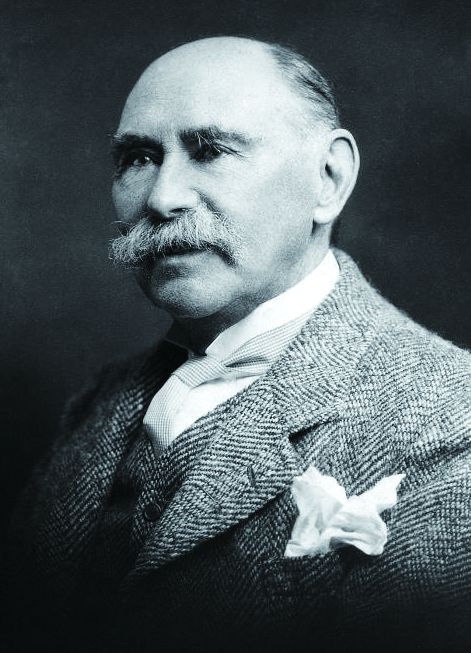
道格拉斯·海德
爱尔兰的民间故事,长期处于无人探索、无人问津的状态,《炉火旁——爱尔兰盖尔语民间故事集》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种文化缺失的遗憾,为爱尔兰文学、盖尔语、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该书的编者道格拉斯·海德不仅是一位知识广博的学者,还是爱尔兰的第一任总统,他在编者前言写道,“只有那些思想单纯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才能为民间故事织出最合体的外衣,他们如此单纯,所以才会兴高采烈地保留着那些心思复杂的人无一例外已经忘记了的故事”“像这样的神话故事理应被妥善保存,因为它们体现了文明人与史前人之间最后一丝可见的联系。这些故事作为古迹的价值,唯有零星几个被钻了孔的岩石或燧石箭簇能与之相媲美”。本书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
爱尔兰和苏格兰盖尔民族间的联系密切之极,体现在文学上必然有某种一致性,事实上,直到英国在阿尔斯特大建殖民地,切断了苏、爱盖尔民族间的交通要道之后,这份历史悠久的亲密友谊才被迫中断。即使在15、16世纪,诗人创作的故事也很有可能刚在爱尔兰赢得声名就被带到苏格兰去碰运气了,这就好像一个英国剧团会从伦敦到都柏林来碰运气一样。
爱尔兰民间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我认为其中一类的起源明显不在爱尔兰岛内,另一类则明显源于爱尔兰。我们之前讨论的都是后一类。大部分篇幅较长的、关于芬尼亚勇士的故事都属于后一类,这一类还包括所有那些内含长篇华章、华章中头韵文字与修辞诗句比比皆是的故事。前一类起源明显不在爱尔兰本土的故事包括那些简单的故事,比如保留了自然神话痕迹的故事;也包括那些看上去源自古老雅利安传统的故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其他说雅利安语的人群中发现了类似的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想弄明白什么是“害怕到发抖”的男人,有些故事讲的是动物、会说话的鸟、巨人或者巫师等等,还有些故事既简单又直白,说明它们广为流传、起源不明,当然,这些故事中有的可能生发于爱尔兰的土壤。属于这一类的还有众多各种各样的传统,这些传统不是故事;除此以外,也有聊天时说到的逸闻趣事,它们不是成套的故事,有些说的是“仙子们长什么样”,“仙子”也被称作“好人”或“达努女神的后代”,有些说的是恶作剧的小精灵、小矮妖、鬼魂、幽灵以及水马等等。据我观察,这些民间想象中的生灵很少出现在真正的民间故事里,或者说,最多作为搭头出现,因为所有常规民间故事的兴趣基本上都集中在某个英雄人物身上。关于小矮妖、仙子等生灵的故事都非常简短,通常还会描述与它们相关的地名和景物,这类故事是人们谈论其他事情时顺带闲聊的话题,讲述真正的民间故事可不是这样,每一次讲述都带着一种庄重的劲儿。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最晚近的民间故事,它们就像吟游诗人吟唱过的故事留下的残骸,现在不妨看看那些最古老的、看似起源于史前时代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有一部分故事毫无争议地体现了原始人竭尽全力解释自然现象的种种尝试,他们或者将自然现象拟人化,或者在自然现象上附加种种解释性的寓言。我们一起来看一个样本,样本故事是我在梅奥郡发现的,没有收入这部集子,故事名叫“长期喝母乳的男孩”,按照冯·哈恩的分类,这个故事大概会归入“勇士历险记”一类。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为了置他于死地,国王派给他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派他去地狱用棍棒驱赶幽灵。有一次国王要他把满满一湖水都吸干,湖的一侧非常深,像个蓄水库,他在这一侧打了一个洞,把嘴贴近洞口,不仅吸干了整湖水而且把湖里的船和鱼等,一切物什吸了个干净,这个湖最后变得“像你的手掌一样干巴巴的”。就算一个惯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得承认,这个故事(不可能有别的含义)是(很有可能是雅利安)太阳-神话的遗存,烈日被人格化,他烤干湖水,把湖变成沼泽,湖里的鱼因缺水干死,湖上的船也搁浅了。像很多别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的意义也不止于此,对于像莱斯教授这样的研究者而言,这个故事为他们把赫拉克勒斯视为太阳神提供了依据。故事中的英雄下临地狱,用手中的棍棒威慑幽冥之灵,国王一再派他执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图置他于死地,他却成功地完成所有任务,这都说明他似乎就是古典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不过,爱尔兰传统中保留了湖水干涸这一故事单元,这必然是太阳神所为,也应当是赫拉克勒斯所为——但理由却不那么充分了。如果不把这个故事看成自然神话的遗存,就完全无法理解它,因为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就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有人吸干了湖里的水和船,吸干了湖里所有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却奇异地传承下来,由父亲传给儿子,很可能传承了几千年,故事成形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一定与今天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或者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一样原始蒙昧。
现在该说一说这些故事的讲述人了。从我做的调查研究来看,唯有在最年长、最被忽视、最贫穷的以爱尔兰语为母语的人当中才能找到有能力讲述这些故事的人。说英语的人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或者把故事简化压缩得干干巴巴以至于价值尽失。我以前在罗斯康芒郡常常听人讲故事,现在这些讲故事的人几乎都过世了。10年、15年以前,我常常听到许多故事,却不知道它们的价值。现在,我回到家乡去找它们却找不到了。它们已经逐渐绝迹,这些或许曾在小山坡间流连了几千年的故事,我们永远听不到了;用爱尔兰人的话来说,青草离离流水迢迢,讲过的故事不会再讲。我从一个老人那里收集了几个这样的故事,老人名叫肖恩·坎宁安,住在罗斯康芒郡与梅奥郡相接的地方。直到15岁以前他都没说过几句英语,他就读的秘密学校的老师来自爱尔兰南部,用的教材是爱尔兰语手抄本,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位老师似乎主要要求他背诵爱尔兰语诗歌。后来的老师却在他脖子上绑了一根棍子,每天早上他到学校后老师都要先检查棍子,装作听棍子说话的样子,要棍子汇报他在家说了多少次爱尔兰语。有些学校的老师则要求家长在棍子上做记号,只要孩子没说英语就在棍子上刻一道印记。他那会儿就挨过打,只要说了一个爱尔兰语单词就要挨打,即使那时候他几乎还不会说英语。如今,他的儿女都说爱尔兰语,不过,说得不是很流利,而他的孙辈们就根本不懂爱尔兰语了。他说,他曾一度“有一麻袋的故事”,早都忘记了。
他给我讲了一两个故事,他讲的时候孙辈们就靠在他膝旁,不过,很明显,他们一个字也听不懂。他的儿女们嘲笑这些故事都是胡扯。要找最纯正的民间故事,如果还能找到的话,就得去西北部的阿基尔岛,可即使在那儿,年轻人也听不懂这些故事了。我在阿基尔岛听一个45岁左右、肤色黝黑、相貌堂堂的男子讲了不少故事,他还能背诵莪相的诗歌,他告诉我,如今他去参加晚上的聚会,每当老人们要他背诗,男孩子们都会跑出去;“他们大概听不懂我说什么,”他说,“他们听不懂的时候,就宁可去听牛低声哞哞。”这就是现状,同样是在一个很多人根本不会说英语的岛上。我不知道阿基尔岛的老师们是不是也在木头上刻记号,不过现在基本不需要了。这个用来消灭爱尔兰语的办法曾在康诺特省和芒斯特省内得到普遍实行,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样的事情居然在奥康纳尔和那些议会议员们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当然,也在那些天主教神父和教长们的眼皮子底下,而且得到了他们的许可;据圣路易教堂的基根神父说,这些教长中有些人是以驱逐本教区的爱尔兰语教师、烧毁他们的课本闻达于教会的。这真是命运的讽刺,现如今如果一个外地人说起了爱尔兰语,他一定很有机会被视作敌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现在新教徒为了改变“(爱尔兰)土著们”的信仰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发行爱尔兰语《圣经》并派遣一些会爱尔兰语的传教士深入民间传教。换言之,外地人在爱尔兰说爱尔兰语要承担极大风险,会被人当作劝诱天主教徒改宗的英国人,如此合理的荒谬之事在别处一定闻所未闻,只有在爱尔兰这个异类身上才会发生。形势依然毫无顾忌地朝这个方向发展着,在这样的形势下,1847年,也就是饥荒年间,还有不少于400万人(比全瑞士的人口还要多)使用的纯正的雅利安语言,在几年时间里就和康沃尔语一样成了死语言,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可以确定的是,这并非无可避免的,其既无社会必然性也无经济必然性。举世皆知,双语者比只会一种语言的人更具优势,然而在爱尔兰,人们却假装相信后者比前者强。只要这个民族的重要领导人物下次来阿基尔岛的时候说上几句话,就可以让爱尔兰语永葆青春。与爱尔兰语共存的还有古老的雅利安民间故事、莪相诗歌、数不尽的民谣民歌和谚语,以及其他大量有趣的事物,只要爱尔兰语活着,它们就活着,一旦爱尔兰语死了,它们也就死了。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收集爱尔兰故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们只听说这些故事大致是某某讲的,谁讲的呢?唉,总之就是一个很老的人。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方设法找到这个人,结果却发现,这个人很有可能正忙着呢。如果赶上农作物收割的时候,根本不用去找这个人,除非你准备和他一起熬个通宵,因为他肯定心烦意乱,满脑子都是收割作物的事情,以至于根本不能告诉你任何东西。如果是冬天,幸运如你赶上他不忙的时候,就得巧施妙计让他把故事讲给你听。
要把爱尔兰语好好地译成英语实非易事,无论是语言的意境还是风格,没有哪两种雅利安语比它俩更水火不容了。尽管如此,盖尔语的语言习惯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四分之三的爱尔兰人说英语的方式,很多让英国人吃惊的表达其实译自我们的父辈、祖辈、曾祖辈说的爱尔兰语,其久远程度因地域不同而不同,这些表达自我延续至今,甚至活跃在爱尔兰语几乎销声匿迹的地区。不过,也有成百上千的盖尔语习语在人们说的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表达,要把它们译得恰到好处是很困难的。艾莱岛的坎贝尔在翻译时就走了极端,为了保留盖尔语的生动性和画面感,他总是拘泥于原文,有时候过于“直译”。比如,遇到“bhain se an ceann deth”时,他不加区别都译作“他把他的头割了下来”,我注意到,这个表达方式被一个现代爱尔兰诗人、议会议员采用。可是,“bain”是个多义词,虽然有“割”的意思,也有“摘、取”的意思,既可以用来表达“割下头颅”也用于表达“摘下帽子”。再比如,坎贝尔总是把“thu”译作“thou(汝)”,平白给故事添了一股酸儒气,这样译其实有些矫饰,于盖尔人而言,盖尔语“thou”就是英语“you(你/您)”,除非特指一人以上,一般不做第二人称复数“你们”理解。坎贝尔的翻译出类拔萃忠实可信,但诸如此类的瑕疵却让人怀疑故事的血统不够纯正,这恰恰是我努力避免的。
为了这个目的,我在翻译爱尔兰习语时并非总是选择直译,尽管我用的英语有很多不符合英语母语者的习惯,但这样的英语却是全国各地的爱尔兰人都在使用的。比如,我没有把爱尔兰语“他死了(he died)”译作“他得了一死(he got death)”,尽管这是字对字的翻译,但爱尔兰英语中没有这种表达。但是,我会把爱尔兰语“ghnidheadh se sin”译为“他过去常常做那件事”,这是普通英-爱人表达“过去习惯”的句式结构,英语中没有这种“过去习惯时”。至于过去完成时我基本用不到,爱尔兰语没有过去完成时,说英语的人看上去也不觉得需要用它,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若是知道早就说了”(I’d speak sooner if I knew that),意思是“如果事先知道的话,我早就说了”(if I had known that I would have spoken sooner)。我的译文中不会出现(坎贝尔式的句子)“做这件事是我的成功(it rose with me to do it)”,我把它译为“我成功地完成了这件事”(I succeeded in doing it),这是因为,前者虽是对爱尔兰习语的直译,却尚未成为英语的习惯表达。我会说“他做了这件事而且他醉了”(he did it and he drunk),而不说“他喝醉酒的时候做了这件事”(he did it while he was drunk),因为前者(对爱尔兰语的直译)是爱尔兰说英语的人普遍使用的句子。有时候,某个爱尔兰语词句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表达,我就像人们在一般语言情境下常做的那样,尽我所能地用英语解释爱尔兰语原文。